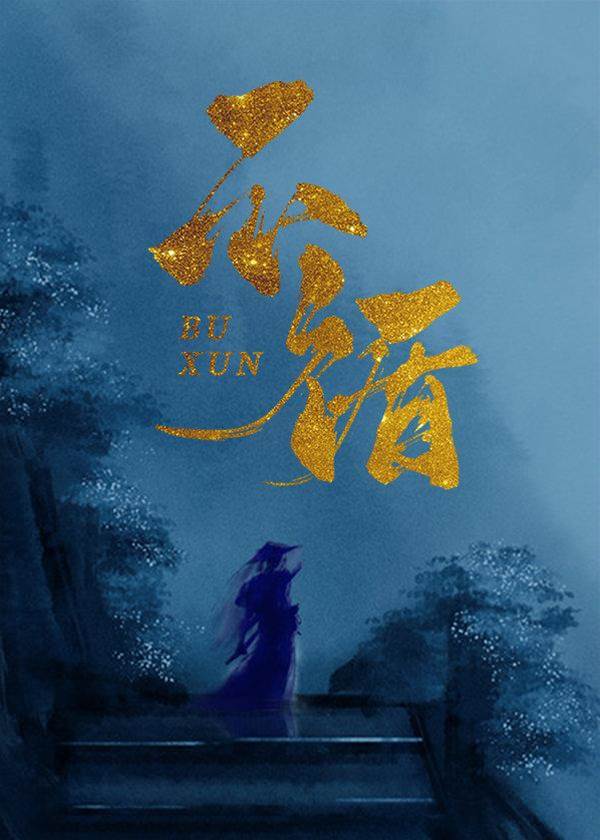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將門嬌嬌一睜眼,偏執王爺來搶親》 第911章 興師問罪合適嗎?
軍醫一面放下大藥箱,一面說:“請世子到榻邊坐下,寬。”
“嗯。”
謝長羽起到床榻那兒去。
秋慧嫻微微皺眉,也隨之過去。
謝長羽抬手拆解護皮甲,秋慧嫻走近道:“小心傷口,我來。”
“好。”
謝長羽果斷撒開手,還展開雙臂,讓來。
秋慧嫻如今對卸甲已經很是練,不論是甲胄還是這類甲。
皺著眉頭拆解那些甲,思忖著為何醫讓寬。
傷口都是能看得到的,不必寬也可以置。
難道是還有別的傷勢?
可是看著謝長羽這姿態不像是有什麼別的嚴重傷勢的樣子?
謝長羽卻是低著頭,眸微妙地注視著秋慧嫻的微皺的眉頭,眼底的溫度走近的醫都眨了眨眼,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
謝長羽朝醫看了一眼,冰冷依舊。
醫連忙躬低頭,安靜地候在一旁。
秋慧嫻為謝長羽卸了甲,又將外袍小心去,猶豫了一下,才解開中系帶。
當襟拉開的那一瞬,秋慧嫻猛然頓住了呼吸。
因為他前也有一道極長的抓痕,和手臂與脖子上的抓痕一樣,但已經結痂,想來是傷有幾日了。
疤痕猙獰丑陋,實在刺眼。
秋慧嫻幾乎可以想象,先前被抓出的皮有多可怖。
秋慧嫻柳眉擰,瓣也抿,盯了謝長羽一會兒,轉頭看向醫,“您要來理的也是這些傷吧?”
醫忙說:“是。”
秋慧嫻點點頭:“有勞了,傷藥放下您去忙吧,我來理。”
醫神遲疑。
秋慧嫻又認真說道:“我懂的怎麼理傷口,您放心。”
醫看了謝長羽一眼,見他沒有異議,便把傷藥留下,悄然退走了。
Advertisement
謝長羽坐在榻邊。
秋慧嫻半跪在謝長羽面前,先把右臂上的抓傷上藥包扎,再包扎脖子上的,最后才置那前的傷痕。
前的傷痕已經結痂,軍醫留下的也是藥膏,并非藥。
秋慧嫻用指尖蘸了藥膏,一點一點涂抹在那傷痕之上,讓那些藥膏化進皮之中。
指尖清涼。
就這般半蹲在謝長羽面前,挲在他前的手指對謝長羽而言不像是上藥,更像是某種另類的。
謝長羽慢慢傾。
那垂在側,未曾傷的左臂也抬起,攬在秋慧嫻后背將擁地靠近自己。
秋慧嫻雙手下意識地撐在謝長羽肩頭,抬頭的那一瞬,有輕的吻落在的眉眼之。
秋慧嫻的心驟然一跳。
抬頭看著謝長羽,雙眸之中顯出無數遲來的擔憂,以及幾分明晃晃的怨念。
那是察覺自己被瞞而生出的怨念。
秋慧嫻抿良久,才問道:“什麼時候的傷?”
謝長羽低聲說:“剛回到營中,帶新兵進山訓練的時候發現了白虎,便了傷。”
秋慧嫻問他:“我今日要是不來,你也不會告訴我對不對?”
謝長羽沉默。
秋慧嫻便知道自己說對了,一時間心更是不好,“為什麼?為什麼不派人說一聲?”
謝長羽不與說的確有幾分故意的意思。
當然謝長羽心底也有的期待。
他想看一看,自己留在營中養傷,多日不回,又會如何反應。
是乖乖做個賢惠妻子,守著家里,還是會想起他,來看一眼呢。
秋慧嫻是來了。
但又是一副“你是我夫君所以我應該關心你,照看你”相敬如賓的樣子。
那公事公辦的,像是早早打好了草稿一樣的聊天模式……
Advertisement
這更是謝長羽有些惱火,便也是公事公辦地與說自己要出去。
謝長羽打定主意,不問那就隨。
但現在謝長羽看滿眼擔心,眼底甚至有些潤的模樣,心底又了一大片。
謝長羽的手上秋慧嫻的臉頰,“怕你看到了害怕,所以暫時就沒回家去,想著等傷口好一點,獵到了白虎——”
“所以你是去打獵。”
秋慧嫻盯著他,“我以為你是有公務要忙!”
謝長羽怔了一下,從話語之中聽出點別的意思——
你什麼都不告訴我!
你把我丟在營中卻是去打獵,不是去辦什麼正經事!
謝長羽沉默了會兒,說:“那山中是我們訓練的場地,白虎出沒是大患,獵得白虎消除患就是公務。”
“這件事是早就決定好了的。”
“鐵籠,人手,也都早先就到位了,不是一時興起去玩耍打獵。”
秋慧嫻張了張,也意識到自己話說的有點無理取鬧,卻是抿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謝長羽左臂用力,帶起抱進自己懷中。
秋慧嫻一驚,想掙扎又怕弄到他傷口,盯著他說了一聲“放手”。
謝長羽自是不會放手。
他低頭靠近面前,“夫人自己對我不聞不問,現在又嫌我不告訴你,這樣興師問罪合適嗎?”
明明他問過,有沒有話要說。
還問了好幾次。
也是自己說沒有,并不曾追問他任何事。
現在竟是埋怨他了,還有幾分理直氣壯的意思。
這就頗有一點當初母親不講道理和父親嗆聲的覺了。
謝長羽不覺得生氣,倒是心更加愉悅。
謝長羽并不是個惡劣的男人,至在通之事上,他不喜歡太過藏著掖著,既然都這樣“不講道理”了,那自然要給臺階下才行。
但這臺階也不是那麼好下。
“半個月,我起碼讓人傳過話回去,夫人卻是未有只字片語給我。”
“你對煥兒倒是真的關心,的確是良母,可這賢妻就不太稱職了,是不是?夫君傷,你是最后一個知道的。”
“夫人要是關心自然第一時間就會知曉丈夫的一切。”
秋慧嫻:“……”
如何沒聽出謝長羽這話是調侃不是怪罪。
這是嫌不關心他。
秋慧嫻稍稍有些自責,只是這種事怎麼好認錯?
道:“我自然是關心夫君的,只是以為夫君有要事,所以我不好打擾——”
謝長羽打斷,淡漠道:“夫人是不想關心。”
所謂的“以為夫君有要事”,只是給自己找好的理由而已。
謝長羽毫不客氣地破了。
秋慧嫻咬瞪著他,覺得這個男人平素都好說話,怎麼現在為這個事揪著不放。
兩人四目相對,秋慧嫻掌下便是謝長羽結實健的肩胛。
腦中忽然叮了一聲,鬼使神差地上前去,親了他瓣一下。
謝長羽微怔。
“我……”秋慧嫻抿抿,盯著謝長羽的眼睛:“我是你的娘子,自然關心你,只是怕你覺得被管著,會覺得煩。”
“我以后不會不聞不問。”
謝長羽深深地看了一眼,“不夠。”
秋慧嫻遲疑:“什麼不夠?”
“這個。”
他的手指過秋慧嫻的角,“怎麼夠?”
話音落下時,他低頭吻住妻子的瓣,比初見時到了帳那親昵更加的熱切濃烈。
猜你喜歡
-
完結1354 章

神醫嬌媳:寵妻狂魔山里漢
“美男,江湖救急,從了我吧!”情勢所迫,她反推了隔壁村最俊的男人。 ……穿越成小農女,長得有點醜,名聲有點差。她上山下田,種瓜種豆,牽姻緣,渡生死,努力積攢著功德點。卻不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勾走了她的心,勾走了她的身,最後還種出了一堆小包砸!
115.2萬字7.82 116552 -
完結789 章

重生王妃又闖禍了
“王爺!王妃把皇後打了!”男人冷眼微瞇,危險釋放,“都是死人?王妃的手不疼?”家丁傻眼,啥……意思,讓他打?“王爺,王妃把宮牆城門砸了!”某男批閱摺子動作不停,“由她去,保護好王妃。”“王爺,王妃被抓了!”“好大的狗膽!”屋內冷風四起,再睜眼,某王爺已消失在原地。自那之後,某妃心痛反省,看著某男因自己重傷,她淚眼婆娑保證,“夫君我錯了,下次絕對不會這樣。”然——好景不長。“王爺,本宮又闖禍了!”
138.1萬字7 264466 -
連載1606 章

有了讀心術後王爺每天都在攻略醫妃
21世紀醫毒雙絕的秦野穿成又醜又不受寵的辰王妃,畢生所願隻有一個:和離! 側妃獻媚,她各種爭寵,內心:我要噁心死你,快休了我! 辰王生病,她表麵醫人,內心:我一把藥毒的你半身不遂! 辰王被害,她表麵著急,內心:求皇帝下旨,將這男人的狗頭剁下來! 聽到她所有心聲的辰王憤恨抓狂,一推二撲進被窩,咬牙切齒:“愛妃,該歇息了!” 半年後,她看著自己圓滾滾的肚子,無語痛哭:“求上天開眼,讓狗男人精儘人亡!”
146.5萬字8 841031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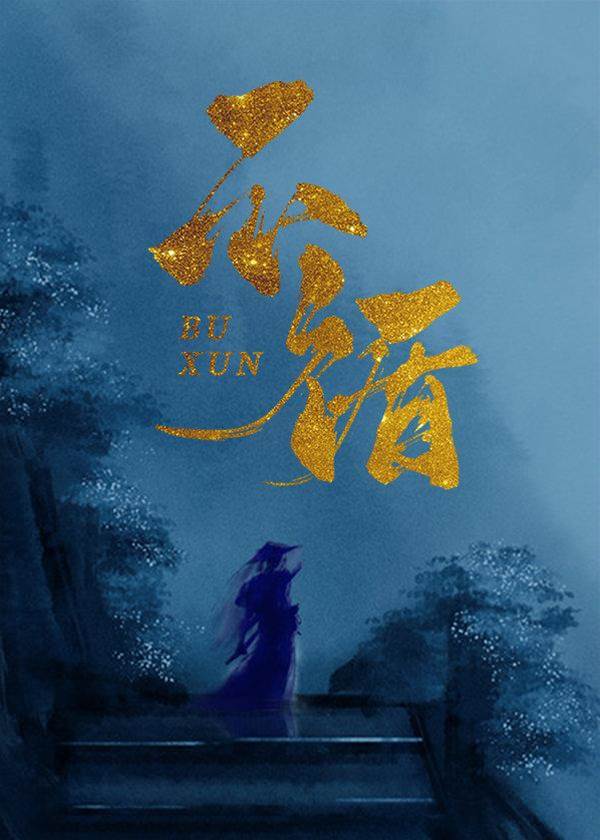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59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