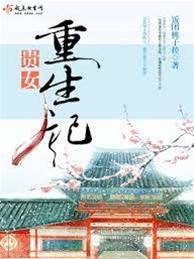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失憶后被權臣嬌養了》 番外三
姜鶯的云鬢垂落于枕間,男人指尖纏繞著一綹漫不經心把玩,他姿態隨意,懶懶地靠在床圍上,一副任君采擷之姿。
不過眼神卻時刻釘在姜鶯上,從上到下,從里到外,明明姜鶯上寢完好,卻有一種暴在他眼皮子底下的錯覺。
小手了終是沒繼續的勇氣,寢帶子解到一半落荒而逃。
姜鶯在錦被中只出半張臉,渾上下都染上一奇異的薄紅。尤其在聽到男人那聲輕笑后,更是的整個人藏進被子里。
王舒珩俯,隔著那床大紅緞繡鴛鴦雙喜被把人抱住,他笑出聲來:“躲什麼?不是你說要哄我的?”
“不哄,我要睡了。”小姑娘聲音悶悶的。
安靜片刻,王舒珩還是朝出手,低沉的嗓音帶著蠱,他道:“一起。”
懷中的子桑若無骨他已十分悉,甫一近手指輕輕撥弄事就順理章。王舒珩的吻接二連三落下,引的不住栗。
須臾,姜鶯香細細地喚了聲:“夫君。”
面若緋云,胳膊像無的藤曼纏上,好像只有這樣攀附對方才能依存。
可是那人壞呀,無視的求助,糲的指尖按在的心口,與調笑道:“鶯鶯這是怎麼了?心跳那麼快。”
姜鶯抬眸睨他,微微抖的子怎麼也停不下來,只得滿心惶恐的湊近,以吻封緘那人的。
折騰了幾回,姜鶯香汗如雨,嗚咽著哭個淚人,對那逞兇之徒拳打腳踢。
好不容易撒完氣,打著淚嗝,本以為會被抱去凈房沐浴,只是王舒珩再度住的腳踝時,姜鶯心頓時警鈴大作,眼淚跟斷了線的珠子似的往下墜,說什麼也不從了。
Advertisement
但久旱逢甘霖的男人并不理會,這一場竟鬧至黎明才停。迷迷糊糊中,姜鶯還記得男人輕輕抱著哄,說子骨太弱打算教習武鍛煉。
半夢半醒中,姜鶯恨不得拿鼻孔瞧他,便宜都占盡了還挑刺……
春雨來襲,一夜過去院中海棠落了滿地。清晨天微亮,雙寧院丫鬟婆子就忙開了。
這些新府的人皆由小鳩茯苓管教,因懼怕沅王殺名,干起活來規規矩矩,就怕不小心出錯惹怒主子沒命。昨晚水房值夜的是兩個婆子,一大早趁水房清閑嘀嘀咕咕:
“雙寧院可真能折騰,昨夜要了五回水呢。靜真大,昨晚水房的爐子就沒滅過。”
那些婦人長舌,一人帶頭其他的也跟著附和:“可不是,那滴滴的小王妃都哭什麼樣了,這會還沒醒呢。沅王看著冷心冷,想不到這檔子事上這麼狠。”
“要我說這也怪不著沅王,那江南米水養出來的小娘子的能掐出水來,瞧瞧那玉豆腐似的胳膊,我要是個男人也把持不住。”
……
這幫婦人越說越不靠譜,汴京人說話做事直腸子,饒是茯苓這樣沉穩的大姑娘,乍一聽也是臉上一熱。
殿下寵王妃自然是極好的,茯苓比姜鶯大幾歲,事事為自家姑娘考慮。離開汴京時孟瀾還拉著的手說了,后宅務必多多提點姜鶯。
茯苓在外頭吹了會風,甫一踏進水房所有的聲音驀地消失,婆子們心虛地低頭等候吩咐。
“熱水燒上,王妃再過一會就該起了,還有米粥溫著,小廚房把午膳也備好。”
瞧面嚴厲,一幫婆子也不知剛才的話沒聽去,茯苓走后一整日都戰戰兢兢。
Advertisement
雙寧院臥房鮮花堆錦,淡淡的熏香充斥四周。姜鶯這一覺睡的天昏地暗,醒來時邊已經沒人。
看天這會快到中午,王舒珩應是一早到天策府上值去了。著床榻空的一側,昨晚的畫面一閃而過,姜鶯臉上又燒起來。
昨晚被折騰的意識模糊,最后完全不記得是怎麼結束的。此時床榻干凈清爽,想必是睡著后王舒珩親自換過。
姜鶯擁被坐起,喚小鳩進屋伺候。
錦被只蓋過口,出一雙雪白的香肩。那上頭印記點點,小鳩瞧見別過視線再也不敢抬頭了。
強撐著酸的起,姜鶯梳洗完畢,坐在梳妝鏡前裝扮。
小鳩道:“廚房已經備好午膳,奴婢先人裝進食盒,馬車也備好了,一會王妃梳妝完畢直接出門去天策府就行。”
這幾日中午姜鶯都去天策府給王舒珩送午膳,小鳩自然而然以為今天也要去。
不想話音才落,姜鶯就賭氣似的,“今日便罷了,你幫忙送過去。”
偏偏小鳩是個實心眼,追問:“若殿下問為何王妃不親自送午膳,奴婢該怎麼說?”
姜鶯剜一眼,徹底不要臉皮了,“他自己知道。”
午后漸熱,姜鶯用過膳食沒一會小鳩就回來了,還帶來一句話:殿下讓您好好歇息。
然有段緋緋在汴京,姜鶯是休息不的,這姑娘三天兩頭就來王府鬧騰。兩人在王府坐了一會,段緋緋便提議帶姜鶯去汴京最大的酒樓天韻館用晚膳。
段緋緋常來汴京,吃喝玩樂跟著準沒錯,姜鶯收拾妥帖兩人便出門了。
*
傍晚,落日余暉籠罩著汴京,這座城市夜后愈發繁華,街巷筆直錯,輝煌宇榭直上青云,眼前未夜便燈火通明的樓閣便是天韻館了。
近來天策府事務不像之前那般繁多,過了酉時王舒珩要走,正巧上中郎齊大人邀約。原來今日是中郎齊大人生辰特在天韻館設宴,王舒珩不好推辭只得一同前往。
天韻館以江南風為特,菜品清爽偏甜,口味十分正宗。聽那小廝口音是南方人,王舒珩便想著有空要帶姜鶯過來試試。
汴京人尚文好狎,尋常宴席都有子奏樂作陪,今日也不例外。齊大人來陪酒的是胡姬,姿明艷照人,舞步隨琵琶小調律輕如飄雪。
藝俱佳的胡姬待客十分熱忱,于曼妙歌舞中起向諸位敬酒,一杯接一杯不醉不休。
這種風月場的子早練就一雙火眼金睛,知道什麼樣的人該用什麼的手段接近。有胡姬勸酒,不多時,諸位同僚便眼神迷離有了醉意。
觥籌錯間,唯王舒珩一人還算清醒,他并不言語,只是不不慢地喝酒,目不經意瞧見胡姬那裳。
自從親后,王舒珩并不否認自己對姜鶯的念。男人就是這樣,再怎麼清心寡一旦沾上,思想就變得齷齪起來,更何況他從來也不是什麼好人,對姜鶯食髓知味,甘之如飴。
此時瞧著那流溢彩的霓裳舞,不想知道若穿在姜鶯上是什麼樣子。
腰細,玉骨輕,舞裳恰好能將姿顯無。
王舒珩便想著,要為姜鶯做一件舞裳,以金線勾綴,珍珠寶石做襯,以后只穿給他一個人看……
他的目太過專注難免人誤會,胡姬原本是不敢上前打擾的。們識人準,看得出這男子雖生的一副皎然出塵的好相貌,但那雙薄眼疏離盡顯,還帶著不可一世的清高。
但許是長時間的凝給人勇氣,一位胡姬舉著玉杯上前,聲音甜膩的好像摻了:“大人,云月敬您一杯。”
置之不理已是王舒珩最大的讓步,瞧見有人敢向沅王敬酒眾人便紛紛看過來,這下那名云月的子愈發尷尬了,舉著玉杯要放不放,又不能自己喝了。
有這麼多人著,王舒珩是不給一點面子,淡淡道:“不必。”
還是一位同僚看不下去,干笑兩聲接過把人招到自己邊。這會壽星齊大人已經喝多了,醉醺醺湊近,說:“殿下是不喜歡胡地的子嗎?”想到沅王妃,又悄悄道:“天韻館也有江南的,要不給您安排兩個?”
他道了兩聲不用,再次祝賀過便打算告辭了。變故也就發生在那麼一瞬,前方一抹悉的影閃過,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還幽怨地瞪他一眼。
鄰座間以屏風相隔,須臾,悉的人便坐到了隔壁。姜鶯是真的惹眼,如明月,顧盼生輝,才進天韻館沒一會就引得人人競相來。
其實一進天韻館姜鶯就看到王舒珩了,總能在人群中一眼認出夫君。彼時男人隨意靠坐在椅子上飲酒,姜鶯剛想走近,正好瞧見那胡姬上前。
一瞬間,小姑娘的醋壇子打翻了。
同姜鶯一樣,段緋緋也發現了人,不過第一眼看見的是曹郇。這種好機會可不會錯過,特意挑了個距離近的位子,拉上姜鶯過去坐。
人在哪里都歡迎,跑堂熱的招呼:“二位姑娘用點什麼?咱們天韻館以江南菜最為出名,您想吃什麼盡管吩咐。”
一聽江南兩個字,姜鶯便問:“有荷葉酒釀酪嗎?”
“這可是江南名菜本店當然有,不過不巧,這道菜每日限量五十份,已經賣完了,不若您再看看別的?”
姜鶯沒有為難,遂和段緋緋點了幾道菜。距離太近,姜鶯耳朵一就能聽到王舒珩那邊在說什麼。
隔著屏風,能到一灼熱的視線,但姜鶯就是賭氣著不回應。
王舒珩輕笑一聲,也知道要哄人了,便讓福泉把自己桌上那道沒用過的荷葉酒釀酪送過去。
不多時眾人宴飲的差不多,齊大人結完賬一幫人道別,王舒珩卻沒有立刻走,他了下眉心。在天韻館門口等了好一會,才見姜鶯獨自出來,段緋緋早跟隨曹郇去了。
熱熱鬧鬧的燈景下,男人就那麼立在不遠著,邊噙著笑,“吃飽了?”
姜鶯氣鼓鼓走過去,使著小子:“胡姬的舞好看嗎?敬的酒味道如何,我也很想嘗嘗呢。”
“不好看,我沒喝。”王舒珩三言兩語解釋清楚,才來拉的手。
姜鶯掙了下,但對方握的那點力道不值一提。兩人別別扭扭走了一段,王舒珩問:“荷葉酒釀酪好吃嗎?”
“好吃。”姜鶯不假思索地回答,但一想兩人還在鬧別扭,又咕噥著:“我還在生氣呢,別以為這樣原諒你了。”
王舒珩臉上地:“那我哄哄你。”
自從來汴京后,兩人還是頭一次一塊出門。畢竟是皇城下,汴京夜景斑斕,臨江熱風拂面各式表演更是層出不窮。
端節前后,汴京商鋪都會在江邊支起棚帷做買賣,遠遠去燈火花影相輝映,寶鼎薰香。百索,艾花,銀樣鼓兒擺了一路,直人眼花繚。
兩人沿著江邊走,姜鶯循著香味到一食攤前,要了一份香糖菓子,是熱乎乎地捧在手里就覺得滿足。
王舒珩付完錢,轉頭一顆菓子就遞到他的邊。那香糖菓子是端才有的食,以紅棗木瓜做料,再以糖浸之,澤人清香陣陣。
“一口咬下去都是可甜了,你嘗嘗。”小姑娘好哄,這會已經忘記先前的不高興了。
王舒低頭,就著的手吃下,不知有意還是無意,輕輕地了下姜鶯指尖。他點頭:“確實很甜,再來一顆。”
被吻過的指尖沾上他的溫,姜鶯回手不自在地了,把香糖菓子捧到他跟前,“那你自己拿。”
王舒珩笑了下,攬著人繼續往前走,一路上食香味撲鼻,更是可見裊裊煙火。
攤主們瞧他兩穿著富貴賣力的吆喝,喜餅攤前一位大娘像抹了似的,招呼著:“小娘子買一個嘗嘗,我王大娘的餅子味香喜氣足,吃了保證你們小兩口來年抱個大胖小子。”
那喜餅被蔬菜水染的紅通通,上頭灑上白芝麻粒在油鍋里滋滋冒著白汽兒,看著都犯饞。
“來一個吧。”王舒珩早發現了,他的小妻子怔怔盯著,也不知是被那番生孩子的話唬住還是饞。
大娘接過銀子,手腳利索地給包好,還大方道:“小娘子長的俏,大娘多送你一個,來年多子多福。”
姜鶯不好意思地笑笑,雙手接過轉,卻見段緋緋幽怨地站在后,瞧對方那副喪氣的樣子,肯定又在曹郇那兒吃癟了。
“你要吃嗎?”
段緋緋搖頭,現在什麼也吃不下,只想在姜鶯這里尋個安。然而此時姜鶯邊跟著沅王,瞧他兩旁若無人地恩恩,段緋緋更氣了。
之前兩人在天韻館已經用過晚膳都不大,喜餅被切幾塊,又給丫鬟小廝分了些。姜鶯與王舒珩還打算繼續逛,中途冒出一個段緋緋姜鶯便邀一起。
段緋緋剛挫急需找點樂子,本想說好的,但抬眸見沅王那雙冷清的眸子,一下噤聲,半晌才喃喃道:“算了,本小姐自己去玩。”
明明沅王什麼都沒說,但段菲菲就是知道這個男人想霸占著鶯鶯。
一路邊走邊逛,不知不覺人漸漸多起來。王舒珩始終牽著,小廝丫鬟被人群遠遠的在后頭。上了拱橋更是肩接踵,他們被人群推著向前,王舒珩到姜鶯牽他的手了些。
膽子小的跟貓兒似的,王舒珩索把圈懷中,在人群中為分隔一片小小的天地。
“我在呢。”他著姜鶯耳畔道。
周遭人聲鼎沸,這輕飄飄的一句話按理說應該被淹沒,但不知為何姜鶯就是聽到了。抿,仰頭他:“我知道。”
過了拱橋人流如織,不遠有個高高的戲臺子,旁邊還有些小玩意。木偶戲,載竿,還有變臉表演。
逛過一圈姜鶯興致缺缺,想說天不早可以回去了,但轉頭,卻見王舒珩盯著木偶戲出神的凝。這出木偶戲演的是《轅門戟》,以懸控傀儡,搭配口技表演的活靈活現,時不時引的觀眾拍手好。
見夫君看的迷,姜鶯便乖乖窩在他的懷中沒有打擾。沒一會,王舒珩才拍拍的肩,說:“回去吧。”
“可是還沒有演完。”
王舒珩一眼看穿的小心思,“你并不喜歡木偶戲不是嗎?”
姜鶯沒有否認,坦誠道:“可夫君喜歡,陪你看完再走也不遲。”
周遭人聲嘈雜,王舒珩卻覺得安靜下來,仿佛天地間只有他們二人。他心中一暖,從后抱住,道:“那就先謝過小王妃陪本王看戲了。”
他們說話的時候,臺上木偶戲已然來到高。伴隨著綿鼓聲,圓紙影在白布幕上飛快地旋轉,出箭作矯捷氣勢威猛人,人群中驚呼四起久久不能安靜。
王舒珩抱著的胳膊了,說:“小時候有一次和父親出門,看的木偶戲也是這出轅門戟。那時木偶戲在汴京盛行,街邊茶樓隨可見,這幾年倒是了。”
他聲音淡淡的,辨不出什麼緒,但姜鶯心里就是悶悶的。王舒珩手背以示安,對方也的指尖以作回應。
“姜鶯,你愿意隨我來汴京,真的很好。”
木偶戲結束后,白布幕很快被撤下,這次換上來一個手持長劍的年。那年劍眉星目,一紅立于臺上惹眼非常,行走間揮劍而起,宛若游龍穿梭甩出漂亮的劍花。
臺下一陣好之聲,姜鶯看呆了,是頭一次看舞劍不也跟著發出驚呼,“夫君,他好厲害!”
臺上年的長劍猶如白蛇吐信,銀乍起嘶嘶破風,姜鶯看的正是神,卻覺一只微涼的大掌覆住了眼睛。
視線驟然變黑,王舒珩的吻隨而至,他輕輕吻一下姜鶯的耳垂,說:“舞劍有何難,回府我給你表演便是。”
說著,姜鶯已被他攔腰抱起走出人群。聽他的口氣姜鶯就知道,這人又吃醋了。
天已晚,兩人往回走路過一家藥房,王舒珩想到什麼便讓姜鶯在外頭等一等。沒一會,他手里拿著一只瓷白藥瓶出來。
姜鶯不解:“夫君哪里傷了?”
“給你用的。”王舒珩一本正經答,看姜鶯實在疑,便低頭在耳畔說了什麼。
果然,下一瞬姜鶯臉就燒起來,紅的好像煮的蝦子一般。怪不得,昨晚折騰那樣今早除了酸也沒覺得哪里不適,原來是這人趁睡著抹過藥了。
一時間姜鶯不知是該說他還是壞,強裝鎮定,“我沒事了不需要這個。”
王舒珩笑:“還是備著吧。”
說罷牽起的手回府,姜鶯跟在他后一路腹誹,沒走多遠,忽聽后似乎有人:“鶯鶯——”
兩人齊齊轉頭,只見明亮燈火下立著一個清雋的男子。
“表哥?”
看清來人,姚景謙上前拜過,視線自然而然落在二人纏的手上……
猜你喜歡
-
完結483 章

休了那個陳世美
大閨女,「娘,爹這樣的渣男,休了就是賺到了」 二閨女,「渣男賤女天生一對,娘成全他們,在一旁看戲,機智」 三閨女,「娘,天下英豪何其多,渣爹這顆歪脖子樹配不上你」 小兒子,「渣爹學誰不好,偏偏學陳世美殺妻拋子,史無前例的渣」 腰中別菜刀,心中有菜譜的柳茹月點點頭,「孩兒們說得對! 我們的目標是……」 齊,「休了那個陳世美」
89.7萬字8 16991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640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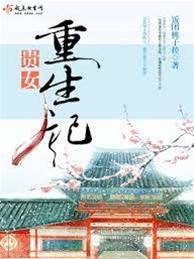
貴女重生記
大晉貴女剛重生就被人嫌棄,丟了親事,於是她毫不猶豫的將未婚夫賣了個好價錢!被穿越女害得活不過十八歲?你且看姐佛擋殺佛,鬼擋殺鬼,將這王朝翻個天!小王爺:小娘你適合我,我就喜歡你這種能殺敵,會早死的短命妻!
62.1萬字8 1383 -
連載773 章

洞房夜,給禁欲殘王治好隱疾后塌了床
穿成丑名在外的廢柴庶女,洞房夜差點被殘疾戰王大卸八塊,人人喊打! 蘇染汐冷笑!關門!扒下戰王褲子!一氣呵成! 蘇染汐:王爺,我治好你的不舉之癥,你許我一紙和離書! 世人欺她,親人辱她,朋友叛她,白蓮花害她……那又如何? 在醫她是起死回生的賽華佗,在朝她是舌戰群臣的女諸葛,在商她是八面玲瓏的女首富,在文她是下筆成章的絕代才女…… 她在哪兒,哪兒就是傳奇!名動天下之際,追求者如過江之卿。 戰王黑著臉將她抱回家,跪下求貼貼:“王妃,何時召本王侍寢?” ...
142.7萬字8.18 133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