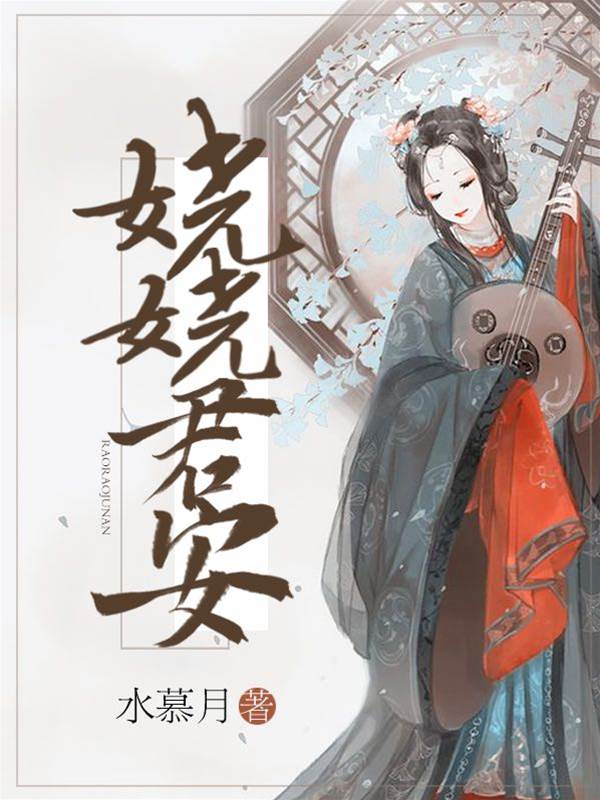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尚公主》 第142章
風清人靜。
太子靠著憑幾,一蜷起,一直。他有些懶散地坐著,頗有些意興闌珊地端詳著立在他麵前質問他的楊嗣。
年時的肆意被青年時的穩重所替代,然而楊嗣到底還是楊嗣,他無法自己坐其,看著他人為他犧牲。
他依然是那個鮮怒馬的楊家三郎。不聽調遣而回長安,他並不在意自己會不會得到想要的結果。
可他還是來了。
太子正要話,正逢外麵煙火綻開,五絢爛。
太子便扭頭去看那上砰然的煙火,看它們繁麗多姿,又看它們塵屑一般地從上掉下來。
初時絢麗,終是潦草。
人生不過如此。
卻也不甘如此。
太子淡聲:“既然已經猜到了我要做什麽,何必回來?我的事自然和楊家不開幹係,也不過是讓你走遠一些,保平安罷了。我若事,好不了你。我若事敗,能牽連你。
“傻子才回來。”
楊嗣道:“傻子才不回來。”
他跪了下來,著太子淡漠的麵容。口著一塊大石,的,想要拚命噴湧出來些什麽。他握拳頭,深吸幾口氣,重新睜開寒銳的眼睛。
他如重劍無鋒,跪得筆直,對太子啞聲:“朗大哥,我不需要你這樣。咱們從就在一起,沒道理這個時候將我擯棄出去。這道理你信,別人會信麽?
“你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都聽你的,你讓我回長安我就回,讓我走我就走。你讓我娶誰我就娶誰,不讓我娶我就不。而這些年,我也得你關照……我知道我能夠肆意妄為,都是有你兜著。我知道我能做瀟灑無羈的楊三郎,都是有你給我收拾爛攤子。
“人常帝王家都是無人,你也無,可是你對我不一樣。旁人如何怪你我無話可,但是唯獨我,不能你一個不字。你對我仁至義盡,我卻轉頭就走,朗大哥,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Advertisement
太子的眼中有了異樣,看他的眼神不再那般敷衍。
太子嘲諷道:“你要如何?”
勸他放棄麽?
楊嗣:“我和你一起幹。”
太子眼神凝住,他怒地一下站起:“胡鬧!”
楊嗣仍跪著,他仰頭,麵容沉冷,眼中神很平靜:“我不勸你,我知道你不容易。你已經忍了很多年,那位卻遲遲不死,現在還要被神醫續命,而你手中籌碼都要被他拔幹淨了……他不拿你當兒子,他一直在製你,打你。
“你心有不平,你不能忍……那就讓我和你一起幹吧。反正楊家和你不了幹係,反正我本來就是你這一脈的。朗大哥,你我之間,沒有什麽‘大難臨頭各自飛’,隻有‘休戚與共’‘死生同袍’。”
太子怔怔看著他。
良久,他袍跪了下來。他與楊嗣額抵額,他抖的,憤怒的,悲傷的。萬般語言不用多,他隻道:“好兄弟,兄長必不負你。”
楊嗣:“我也不負兄長。”
煙火在上綻放,怦然喧嘩,華若流,人間如寄。
-----
煙火在上綻放,怦然喧嘩,華若流,地已寂。
丹公主府中,擺開了案幾在撤掉屏風的大堂中,仆從們退下,由幾位主子敘舊。
韋樹看去,見暮晚搖華裳未換,便與言尚坐在同一案後。
親昵地靠著言二哥的肩,因為煙火聲太大,掩手於頰畔邊,悄聲咬言二哥的耳朵,和言二哥話。
麵頰上著幾分酒意,眸中清盈含笑。
言尚則聽公主的話,他微笑著,低頭在為削果子吃。
暮晚搖還來招呼韋樹,自然坦率:“巨源,就如在自己家一樣,不必客氣。好幾年未曾見你,你竟已及冠了,今日正該讓我好好瞧瞧。”
韋樹心中浮起恍惚,想到了很久以前的某個除夕,就是他與言二哥、公主一起過的。
Advertisement
隻是那時候公主和言二哥尚未明正大在一起,那時候殿下是和自己坐在一起,像是為了避嫌一般,還刻意和言二哥拉開距離。
然而這一次就不一樣了。
這一次,暮晚搖可以明正大地依偎著言尚的肩,將頭靠在他肩上,而不必顧忌風言風語。
韋樹麵上浮起清雅的笑,低聲歎道:“真好。”
言尚過來,眸子如夜一般黑,關心地看著他。
韋樹誠心道:“二哥和殿下婚,我覺得真好。”
言尚麵微赧,他拱了拱手,自然不出什麽話來。暮晚搖卻是大大方方地笑,眼尾染上飛紅:“我也覺得很好。”
歎道:“以前是我年紀,不懂事。以為婚是件極可怕的事。你二哥那時候耳提麵命,催著我定下婚事,我就一直不肯。那時我總覺得,不婚,對我們來沒什麽影響。難道了一紙婚書,我們的就會到影響麽?”
真誠道:“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名分是真的很重要。言二哥哥消除了我對婚姻的恐懼,讓我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一個樣子。他消除了我的很多恐懼……”
想不害怕男人在黑暗中的親吻,因為知道是言尚;不害怕被人從後抱著做了,因為他那般溫;不害怕男人的強勢,因為言尚不會對那樣。
君子若水,上善若水。言尚就是水一般的君子,他日日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他把自己得如同聖人一般自律,而暮晚搖是到他的這種好了。
因為這般好格外巨大,便能接他其他的不好——
比如他對世間萬的博,比如他的朋友眾多。
暮晚搖輕聲:“我們不夫妻,便始終不是一家人,彼此之間始終有隔閡。隻有了一家人,你二哥才能真正接我,真正和我好好過日子。
“你知道他婚前,都背對我睡麽……唔!”
一下子被一枚削好的果子堵住。
瞪過去,言尚道:“好好吃你的,不要胡。”
暮晚搖心知他是不想讓他的私事,咽下了口中的果,瞪言尚一眼,才又像個孩兒般地抱怨道:“你言二哥就是這般死心眼。”
韋樹莞爾。
暮晚搖又像世上所有婚的男那般,自己幸福快樂,覺得婚姻是件好事,便希邊的人跟著自己一樣幸福。
暮晚搖興致地傾看向韋樹:”巨源,你如今都及冠了,有沒有什麽喜歡的郎?韋家不管你的婚事麽?不可能吧?
“你若是看中哪家郎,我可以代你去相看,幫你提親啊。”
言尚在旁打斷暮晚搖的興致盎然:“巨源剛回長安,哪有認識的郎,你不要點鴛鴦了。”
誰知道韋樹沉默一下,開了口:“我倒真有一位喜歡的。”
言尚詫異地揚眉,沒想到韋樹這般安靜斂的人,才回長安就有喜歡的。他心中有幾分不安,卻勉強抑製,笑著問:“不知是哪位郎?”
韋樹臉微不自在。
他道:“是趙五娘。”
暮晚搖當即:“啊……是呀。”
言尚追問:“趙史家中的五娘子,與你一同出使的那位五娘子麽?”
韋樹點頭。
暮晚搖和言尚對視一眼,都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些患。到了如今歲月,昔日趙靈妃拚命追慕言尚的那點過往,兩人都不再計較。
但是韋樹剛回長安,恐怕不懂長安如今的局勢。夫妻二人便下自己的憂慮,對韋樹含笑。
言尚不其他,隻趙靈妃本人:“五娘俏可,又大膽活潑,與巨源倒是彼此互補,極為合適。”
言尚話如此好聽,韋樹自然聽著高興。
暮晚搖在旁抿笑,看夫君斟酌著,似要把難聽的話再補一補,然而就在這時,侍們在外通報:“殿下,言娘子來了。”
言尚和暮晚搖皆詫異,因這般晚了,言曉舟怎會過來?
二人讓人請言曉舟來,韋樹作為客人,則站了起來,眼見著一位腰肢纖細、麵若芙蕖的妙齡郎披著厚氅,款款而來。
言曉舟與韋樹雙雙見禮後,才對自己的哥哥嫂嫂笑道:“是這樣,我們知道哥哥嫂嫂今晚參加宮宴去了,所以沒來打擾哥哥嫂嫂。但是方才我們聽到公主府有靜,便猜到你們回來了。
“阿父晚了,就不你們過去一起守歲了。阿父讓我給你們送歲錢。”
取出兩封紅的信封,裏麵裝著金葉子,笑著遞給公主的侍。而對韋樹抱歉地笑一下,示意自己不知道這位郎君也在,不然多準備一份歲錢更好。
暮晚搖收到言父的歲錢,驚詫又驚喜。
始終覺得自己和言家人的距離很遠,融不進去。但是今夜收到這個,讓覺得言父將當做了兒媳。
暮晚搖珍視無比地翻看紅信封,將裏麵的金葉子了又,歡喜地一遍遍問:“是給我的?真的給我的?我從來沒收到過歲錢哎。”
言尚本來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婚了,還要接父親給的歲錢。
但是見暮晚搖在旁如此高興,他心中一歎,憐惜的不易,就將推拒的話收了回去,向妹妹拱了拱手。
而他妹妹正笑著回答公主:“新婦過門,頭一年過年,不都要給歲錢麽?我們這邊是這樣的。我哥哥怎麽也是娶了嫂嫂嘛。
“嫂嫂雖然以前沒收到過,但必然也收到陛下賞賜的許多禮,不知比這個珍重多倍。我阿父還怕殿下看不上眼呢。”
暮晚搖笑了笑,道:“不一樣的。”
經常接父皇的賞賜,但父皇的賞賜不搖任何基,賞了,父皇也不痛不,父皇也許從來就不知道他給賞了些什麽。隻知道很珍貴。
但最珍貴的,應該是人心。
言家人肯給這顆心,父皇卻不給。
暮晚搖對言曉舟微笑:“明日我與言二哥哥一起登門去拜年,謝謝阿父的歲錢。對了,我們也該給你備歲錢才是——曉舟還沒嫁人,還是個孩子呢。”
言曉舟一瞬間想到了自己那日在街上見到的楊嗣模樣。
紅臉道:“好好的,殿下這個做什麽?”
如此,歡歡喜喜地將言曉舟送出了公主府。而此時已經極晚,言尚看韋樹有些疲憊,便讓侍領韋樹下去休息。
韋樹喜歡他們夫妻兩個,在公主府中格外自在,便也不拒絕。
韋樹走後,言尚和暮晚搖仍回去大堂下的食案前,坐下來一起看上的煙火。
暮晚搖凝上一波波的煙火,手上著言父給的歲錢。
看著韋樹走遠,暮晚搖歎:“趙公如今作為宦的走狗,為士人所瞧不起。巨源喜歡趙五娘,但是韋家不會願意和一個宦走狗結親的。”
言尚低聲:“是。我改日會與巨源明這件事。他不了解如今宦和士人之間的矛盾,如今巨源出使歸來,份遠非昔日可比,吏部正商議著給他禮部郎中做。他正是風得意之時,趙家也風得意……隻是和巨源的風不同。
“雙方立場如此不同,韋家將巨源當作優秀子嗣栽培,必然不會接趙家郎的。若巨源是昔日的巨源,他想娶趙五娘無妨……但他到底才華出眾,一旦顯人前,必然不能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了。”
暮晚搖沉默半。
忽然低聲:“立場不同,也未必不能結姻親。”
言尚心中一,偏頭看向。
盯著他,格外認真的:“隻要有一往無前的決心,有犧牲的決心,兩個人真心喜歡,還是有辦法走到一起的。立場是可以調節可以迂回的,隻要自己真的喜歡這個人,自然會義無反顧地走向他。”
言尚臉微燙。
他想什麽,但到底隻是笑了笑,獎勵一般的,倒了一盞酒,遞到了眼皮下。
暮晚搖眸子彎起,毫不猶豫地接言尚的敬酒,仰頭一飲而盡。
有言尚看著,婚後飲酒不多,每次都是淺嚐輒止,如此才更顯得每次的吃酒機會很珍貴。
酒香甜,郎君的害也香甜。這些都讓腦子暈了,想要更多的。
暮晚搖抓著言尚的袖,好聽的話兒就不要錢一般地流向他:“我十八歲時就喜歡你了!還在嶺南時我就喜歡你了!”
言尚笑,溫聲:“我知道。”
暮晚搖挑眉,言尚低頭:“我那時就知道你喜歡我。你若有若無地勾我時,我心裏是有覺的。隻是你那時姿調太高,我本瞻仰不得。後來、後來……我覺得你的喜歡很不值錢,就算了。”
暮晚搖頓時反駁:“我的喜歡怎麽就不值錢了?”
言尚想了想,:“因為你那時候喜歡我,我覺得和喜歡一隻貓、一隻狗沒區別。你就是看我好玩,喜歡逗我而已。因為你那時太抑,初政壇又什麽都不懂,總被人算計。你需要給自己的生活找點樂子,恰好你覺得我好玩,就來逗我。
“但你其實並不想負責。我剛到長安的時候沒去找你,我覺得,你私下應該都是鬆了一口氣的。”
暮晚搖抿。
以前的絕,確實無話可。隻是言尚的他自己多無辜一般,就讓不高興。
暮晚搖反駁:“你又如何簡單了?你不也一樣。那時你和我話,經常著著就沒話了。不正是因為你心虛麽?我喜歡逗你怎麽了,你那般,不就是等著我撥麽?我看我親你的時候,你明明張了……”
言尚一下子捂的,他臉紅啐:“我那時隻有十七歲,我什麽也不懂……”
暮晚搖拉下他的手,眼眸圓溜溜,又像貓兒一樣嫵:“什麽也不懂你也張了。你分明對我就是有好,就是一直不敢承認。我敢,如果我當時要睡你,你也半推半就應了。”
言尚惱:“胡!我絕不會那般的。”
暮晚搖還要反駁,但是忽一頓,覺得這是在幹什麽,像是要翻舊賬和他吵架一般。而爭的還是誰先喜歡誰這種問題。
暮晚搖不失笑,將頭抵在他頸上,笑道:“好啦,隨便你,反正我心裏知道你有多好推倒就行。”
言尚臉頰滾燙,他側過臉,低頭無奈看:“以後這種話,我們私下就好。不要讓外人聽到了罷?”
暮晚搖地去拿桌上的酒盞,漫不經心道:“不。”
言尚:“……”
他沒話,卻手按在了暮晚搖手上,製止了繼續喝酒。暮晚搖從他手中奪酒壺,他卻不給。
他平時對總是隨隨便便,很有忤逆的時候,隻有這個時候,言尚態度堅定地不給酒,暮晚搖急得眼紅。
斥:“你欺負我!”
言尚低聲:“什麽‘欺負你’?你晚上在宮宴上必然背著我喝了許多酒,我什麽了?宮宴喝了那麽多也罷,回來後怎麽還要喝酒?喝酒傷,你不知道麽?胃痛的時候也不知道是讓誰傷心。”
暮晚搖仰臉,賭氣道:“我之前錯了,和你婚一點也不好。你對我管東管西,我去哪裏都要跟你匯報,你讓我不自由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144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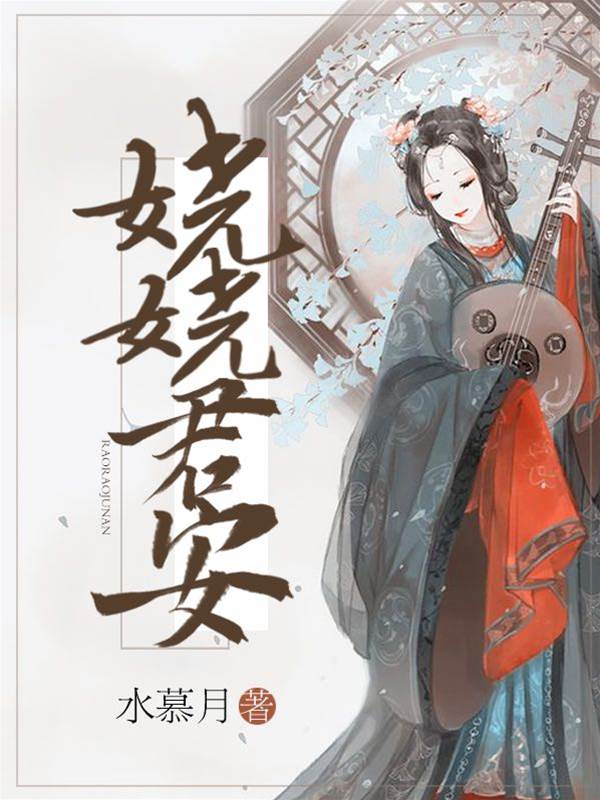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52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4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