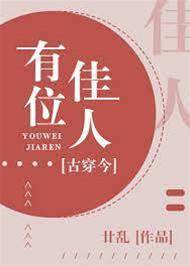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懸日》 第96章 【番外三】N.復刻約會
蘇洄是在結束心理咨詢回家的路上突然轉換躁期的。
原本沉默的他坐在出租車里一言不發,盯著窗外在風中掠過的景,忽然間,原本調灰暗的風景像是突然被添加了明亮的濾鏡,一切變得嶄新而妙,他甚至在等綠燈時忽然聽見了窗外悅耳的鳥聲,以及很多嘈雜而充滿煙火氣的聲響。
世界仿佛是原本折疊著的賀卡,在這個轉換的瞬間被打開了。
蘇洄開始和司機攀談,先是稱贊了他的手表,而后又注意到他后視鏡上懸掛著的相片,那看上去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五口。
“這些都是您的孩子?長得真可,他們多大?您的妻子看上去也很有氣質,你們好幸福啊。”蘇洄微微前傾,注意力很快被車上的手工玩偶所吸引,“這對娃娃好漂亮!”
司機顯然被他突如其來的熱嚇了一跳,明明之前他看上去心不佳,沉默地坐了十五分鐘,一句話也沒說過。
蘇洄下車時,整個人神清氣爽,給司機多付了很多小費,并且站在路邊沖他笑著揮手說再見。
他摘了帽子,覺明,是適合去海邊的好天氣。想到不久前咨詢師格蕾說他最近恢復很多,緒控制明顯好過從前,心便越發激,回到家中,一口氣吃了三盒冰淇淋,凍得牙疼,捂著臉給遠在英國出差的寧一宵打了視頻電話。
“你這次的郁期好像不長。”寧一宵手里轉著一支鋼筆,在心里算了算,“兩個月,而且有一半都是平穩期。”
“醫生也說我恢復很多,但還是囑咐我不能隨便停藥,還給了我幾本心理學的書讓我回家看。”蘇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袋子,“還推薦我學習冥想,或者堅持運,比如長跑,但我實在不喜歡跑步。”
Advertisement
“那就不跑。”寧一宵表很淡,但眼里著笑意,“別讓這些變力,會適得其反。想做什麼做什麼,不想做的事不需要強迫自己做。”
蘇洄很是贊同,“你說得非常對,不過我堆積了好多工作,是時候撿起來了,剛剛我還約凱莎先開個線上會議,打算趁這個機會敲定線上展出的方案,我前段時間畫了一些手稿,也要趕打出框架來,哦對了,貝拉也聯系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參加的秋冬線拍攝呢,我得考慮一下。”
寧一宵耐心聽他說了一長串,轉筆的作一停,“你的日程表里沒有為我們的婚禮留個空檔嗎?大忙人。”
蘇洄這才想到,“對哦!我差點忘了。”
他和寧一宵的相模式完全還是熱期的,總是讓蘇洄忘記兩個人其實已婚的事實。
“那、那我是不是應該先約一個婚禮策劃師啊?還是說我們自己策劃?你應該沒這個時間,要不我自己來……”
“蘇洄。”寧一宵停了他飛奔的思緒。
“嗯?”蘇洄抬頭,隔著視頻看向他,“你有什麼想法嗎?”
寧一宵搖頭,將手里的筆擱在桌上,“這些都放一放,我想和你約會,就這個周末。”
蘇洄眼睛都亮了,整個人往前傾,兩手撐在桌上,“好呀,那你周六回得來嗎?”
“當然。”
蘇洄滿懷期待,掛斷視頻電話又興地給正在康復療養的外婆打了個視頻,聊了幾小時,結束時天都黑了。
他帶著雪糕在外面漫無目的地閑逛,挑了家拉面店獨自坐在窗邊吃拉面,和鄰座的一位日本孩兒聊拉文學,不亦樂乎。
回到家中,蘇洄干勁十足,充滿活力地投到工作中,本不需要睡眠。
Advertisement
但他謹記醫生的話,還是盡可能讓自己保持健康的作息,即便睡不著,也會躺在床上閉眼冥想。
或許是因為寧一宵,他開始不抗拒吃藥,反而很期待自己在未來的某一天可以完全擺這些,他知道這是完全有可能的,自己已經看到了一曙,只要堅持下去,就會有希。
一連好幾天,蘇洄都浸泡在高漲的能量池中,擺了、畏、疲憊和消極的一面,度過著彩鮮艷的每分每秒。
他一時興起買了染發膏,將頭發染深,但又覺得太過平淡,于是挑了靠近耳后的部分和發尾,染。
新的嘗試令蘇洄到非常滿意,心大好,甚至自己試跟著網上的視頻學游泳,套著寧一宵所說的那個小鴨子游泳圈。
當然沒有功。
周五晚上,蘇洄收到了寧一宵的消息。
[puppy:時間有點不夠,明早九點半直接在電影院門口見。]
蘇洄一晚上興得睡不著,一大早便爬起來,挑遍了柜里的服,最后選了一件短袖襯衫,還特意從清晨的花園里挑了開得正好的加百列,扎了一小束帶去。
約定好的電影院在市中心,周末人很多,但過馬路的蘇洄一眼就看到了寧一宵的影。他穿得和平常很不像,沒戴眼鏡,白短袖外面罩著深灰細格紋襯衫、黑棒球帽、藍牛仔和一雙舊球鞋,人群中像個大學生。
蘇洄對他這裝扮到悉,但一下子并沒有立刻想起。
寧一宵的手里還捧了一小束藍矢車,是他全最艷麗的一抹亮。
他們可真是心有靈犀。
蘇洄將自己手里的加百列藏到后,背著手跑過去,蹦到寧一宵跟前。
“你好啊。”
寧一宵還是第一次見他的新發,眼前一亮,出笑容,“早上好。”
蘇洄臨時起意,決定逗一逗小狗,“你什麼名字?”他轉到寧一宵左邊,打量著他,又轉到右邊,“你長得好帥啊,哪個學校的?有對象嗎?”
原以為寧一宵會讓他適可而止,沒想到竟然很配合地跟著演起來。
“謝謝夸獎,附近S大的,有男朋友了,是個藝生。”
他還很一本正經。
“是嗎?”蘇洄抿著笑意,裝出一副可惜的樣子,“果然帥哥都是別人的,你看我怎麼樣?要不甩了你男朋友,和我在一起吧。你男朋友肯定沒我好看,而且我很會談的……”
他正演得起勁,兒沒發現周圍好幾個人盯著自己。
寧一宵倒是察覺到了,拿手里的矢車敲了敲蘇洄的額頭,“玩夠沒有?”
他攬過蘇洄的肩,對一旁站得很近的吃瓜群眾解釋,“他開玩笑的,我們已經結婚了。”
一旁吃瓜吃得正開心的生愣了半天,傻乎乎點了頭。
說完,寧一宵便了蘇洄藏在背后的花,聞了聞,“給我的?”
蘇洄還沒過癮,“你答應甩了他跟我在一起,這個就給你。”
寧一宵無奈道,“行,現在就打電話分手。”
“你好渣啊。”蘇洄接過寧一宵手上的矢車,挽著他胳膊,拉他進電影院的大樓。
“拜你所賜。”
剛進去,蘇洄便聞到一濃郁的焦糖香味,“好香啊。”
“我已經買了一份。”寧一宵看了一眼手機,領著他走向賣零食的柜臺,“正好現在可以取了。”
焦糖味米花的甜氣味發了蘇洄心底的某些記憶片段,但很零碎,直到他看到寧一宵訂的兩張電影票,是他一直很想看、但后來因郁期的突然造訪錯過的文藝片。
一切才真正確定。
蘇洄吸了一大口可樂,“寧一宵,你該不會是在復刻六年前那次失敗的電影院約會吧。”
寧一宵給出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填補空缺。”
也對,誰會復刻失敗呢?
蘇洄突然間發現,寧一宵的強迫癥都是可的,他會記得每一件他們錯過的小事,就像拼拼圖一樣,一個個用嶄新而好的記憶填補進去。
“所以你穿了和那天很像的服。”蘇洄看著手里的藍矢車,“這個呢?你之前也買了嗎?”
“嗯。”
“為什麼沒有帶去我家?”蘇洄眨了眨眼,確信自己沒有記錯,“你是空著手去的。”
“太著急,落在電影院了。”
蘇洄忽然覺得他有點可憐,于是握住了寧一宵的手,了,忽然他發現什麼,低頭一看,寧一宵并沒有戴他們的婚戒。
“誒?戒指呢?”
“車上。”寧一宵說完,也將蘇洄無名指上的戒指取下來,裝進自己的口袋,“既然是填補空缺,就當今天我們還沒結婚。”
蘇洄哦了一聲,可戴習慣了,總覺得手上空落落的,直十手指,盯了一會兒。
“不戴好奇怪呀。”
“戴這個。”
寧一宵又拿出一個小絨布盒,打開的瞬間,蘇洄幾乎要憤而死。
“你怎麼會有這個!”他無法直視自己之前疊的紙戒指。
“外婆給我的。”寧一宵將那枚稍大的套在自己無名指上,又給蘇洄戴上另一只,牽了他的手,拍了一張照片。
然后非常冷靜地給予評價,“這樣比較像大學生。”
蘇洄瞇了瞇眼,“你的意思是只有學生才會做出疊紙戒指這種稚的事嗎?”
“這是很可的事。”寧一宵淡淡道。
聊了不多時,電影便開場,寧一宵帶著蘇洄檢票,黑暗中找到他們的座位。
寧一宵個子太高,坐得太靠前本沒辦法好好看電影,總會被后一排的人小聲提醒,希他可以稍微坐低一點,所以為保證正常觀影,他只能買最后一排。
這部文藝片因最近導演獲獎而有了重映機會,但時隔多年,本眾群也很小,整個影廳的觀眾也不足十人,最后一排更是只有他們兩個。
首映時寧一宵就錯過了,之后盡管一直記得片名,但從來沒試著搜索過,哪怕偶爾看到也會快速關閉,以免景生。
因此他本不知道,原來這部電影有如此多的激戲份。
男主角第二次擁吻的時候,蘇洄的手便不安分地了過來,并不是拿米花,而是越過了安全線,直奔人魚線。
寧一宵一開始佯裝不知,但放任他的結果都得自己承擔,于是他便握住了蘇洄的手腕,圈得很,作有些強。
“別。”他低聲制止。
蘇洄卻為此靠過來,下抵在寧一宵肩上,吹了一口氣,“你干脆把我綁起來好了。”
說完,他打量了一眼,“可惜你今天沒戴領帶。”
說完,蘇洄便拿起那一束加百列,遮住自己的臉,傾吻了寧一宵的側頸,還壞心眼地在上面留下一個紅印,然后歪著頭,故意盯著寧一宵笑。
不過很快他就嘗到了報復的滋味,是一個強勢的、焦糖混合碳酸汽水的深吻。
金屬舌釘和牙齒撞出聲響,在瓣短暫的分離時刻泄,卻又被電影臺詞與悠長的鋼琴曲所遮掩。
電影院隨時會有人起,或是回頭,兩個人不加遮掩又抑的吻,比大熒幕上的戲碼還要令人臉紅心跳。他們結束一個吻之后,蘇洄便回頭,假裝無事發生地繼續看電影,只有心跳和難以平復的呼吸傳遞著方才的躁。
他很這種刺激,就像溺在糖水之中。
電影播到后半段,男主面臨分別,蘇洄突然很不喜歡看這樣的橋段,于是起,說自己要上洗手間,離開了座位。
可他走的時候,眼神卻不舍地流轉在寧一宵臉上,直到完全走出影廳,才收回眼神。
洗手間很大,里面放著迷迭香味道的香薰。蘇洄對這種氣味有些敏,進去便有些暈乎乎的,他站在鏡子前,將自己的頭發挽了一半扎起來,剩下的披著。閑人長頭發,他的頭發又不知不覺留到鎖骨,發尾卷卷的,理不直。
洗過手,蘇洄將手放在烘干機下面翻來覆去吹,吹到第三遍的時候,寧一宵進來了。
“你也……”
沒等他把話說完,寧一宵便把他拽到最里面的隔間,關上門,將蘇洄到門板上悶頭接吻。
“唔……”
這個吻來得比方才在影廳里的強勢十倍,蘇洄幾乎不上氣,手卻不自覺往上攀,勾住寧一宵的后頸,舌釘磕著齒尖,吮吸聲和水聲在安靜的洗手間顯得格外分明。
不過很快,兩個男聲闖進來,分別進他們隔壁和對面的隔間。
寧一宵收斂了許多,退出來,安靜和地啄吻他的。
但蘇洄卻起了壞心眼,直接蹲了下去,牙齒咬住,舌尖嘗到金屬的味道。
寧一宵捂住了他的臉,但蘇洄卻并沒有作罷,反倒干脆含住寧一宵的指尖,手上作沒有停止。
隔壁兩個男生還聊了起來,很重的加州口音,左一個dude右一個chill,每個單詞都是氣泡音。
“我覺這個系列越來越不好看了。”
“我也覺得,還是第一部好看,劇越來越差了。”
“就是,早知道不來了,電影票還這麼貴,影廳環境還趕不上洗手間。”
“哈哈哈哈,確實,洗手間比影廳還香呢。”
對方忽然一頓,“什麼聲音?”
“什麼什麼聲音?”
寧一宵騰出原本控在蘇洄后腦的手,向后索到坐便的應開關。
沖水聲響起。
“可能是我聽錯了。”對方聲音有些不確定,但還是傻里傻氣地笑了起來,沖了水,打開隔間門,和同伴離開了。
腳步聲漸漸遠去,直至完全消失。
蘇洄終于沒忍住,咳嗽出來,嗆得厲害。
寧一宵將他拉起來,埋在他鎖骨吻了又吻,他原本的溫總比蘇洄低一些,可現在全都是熱的,呼吸也是。
“你好難弄。”蘇洄吻著他耳朵。
寧一宵很低地嗯了一聲,“第一天知道?”
他故意逗弄蘇洄,不是言語,“你果然是在和別人的男朋友約會吧,這麼……”
在形容詞的選擇上,他卡頓的時間明顯變長,畢竟差一點走向了dirtytalk的道路。
可蘇洄還非要明知故問,甚至現學現賣了方才的加州腔調,“What?”
“沒什麼。”寧一宵故意不說,只是半掐著他的脖子接吻,吻得蘇洄意迷,又松開,盯著他的眼睛。
反復好幾次。
蘇洄忍無可忍,握了握,“你要一直這樣嗎?”
熱門商圈的洗手間人來人往,很快又闖進來幾個人,嬉鬧聲很大。
[放輕松,你該不會是喝大了吧?不就是接個吻嘛!]
寧一宵低了聲音,“怪誰呢?”
[關鍵是太詭異了,那可是我的朋友!]
蘇洄知道他在猶豫什麼。
笑著,著他耳廓,小聲道:“寧一宵,你現在這樣的確很像正直的男大學生了,接個吻都會糾結的那種。”
[朋友怎麼了!朋友發展人不也很正常,約幾次會保證就不詭異了,你明明就很喜歡,試一次唄!]
猜你喜歡
-
完結132 章
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我深深地愛著你,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傻逼他不愛你,你比傻逼還傻逼, 愛著愛著傻逼的你,我比你更傻逼, 簡單來說,本文講述一個,誰比誰更傻逼的故事。 簡隋英簡大少爺好男色的事情簡家上下無人不知, 連同父異母的弟弟簡隋林帶回家做客的同學也被他看上了。 可惜任簡大少明示暗示,那個叫李玉的男孩始終堅一臉正直的說,我不是同性戀。 開始抱著玩玩心態的簡大少屢次碰壁之後被激怒了,想要霸王硬上弓, 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自己成了被攻的那個。 而原本無比厭惡簡隋英的李玉,卻在三番四次被挑釁繼而發生了關系後食髓知味, 對簡隋英的態度起了變化。而身為同父異母弟弟的簡隋林,對哥哥似乎也有著不同尋常的情愫…… 本文講述了一個直男被掰彎的血淚史,語言京味兒十足。 紈褲子弟簡隋英看似吊兒郎當的一副流氓樣惹人討厭,高幹子弟李玉則是一副清高又正直的樣子
35.2萬字8.18 21891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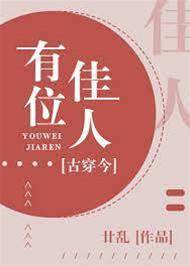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
完結109 章
一頭母豬
沒事就愛“哭”。 母胎單身22年的元豐一直想找個女朋友 來大城市打拼6年了 他拒絕了小珍、小麗、花花、阿玲… 不是不想答應,而是因為他有個難以啟齒的秘密。 狗血俗套無腦.放飛自我瞎寫
23.2萬字8 15275 -
連載147 章

禁止套娃[無限]
過去的經歷讓溫時不再相信任何人。這個世上能信的只有自己。****溫時意外卷入了一場無限游戲。[恭喜玩家覺醒‘我就是我’技能。我就是我:耗費一百積分即可召喚平行世界的‘我’一次。]溫時漠然:“召喚來送死嗎?”直到——恐怖古堡之夜,古堡的主人要…
72.4萬字8.18 1152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