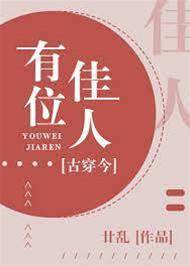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君寵難為》 5-19
“怎麼,這是耍脾氣了?”
韓淵面上帶著笑,湊近了些。
“果然當了宰相,就是不一樣,脾氣也跟著見長。這堂堂宰相大人,說給臉看就給臉看——下真是怕了怕了。白大人,韓淵向你賠不是,行不行?”
“韓淵!”
白皎然卻猛地回過頭,臉上像是掛了寒霜,眼神也冷得很。他抑著聲音中的火氣,
“你今日,究竟為何而來?”
見他這樣,韓淵也不敢再逗弄他。他正經地說,
“是陛下派我來的。”
白皎然神一。徐將軍的話在他耳邊響起——平谷關外常有亡命之徒……坑蒙拐騙……走投無路……死地求生……
且不說當年韓淵放走了杜玉章,陛下大為震怒;就算陛下真的不計較他,也絕不會隨意將這旨意由他傳達——陛下邊待著一整支侍衛隊!方才那腰牌,不就是其中一人的?若陛下真的有旨意,為何不讓侍衛傳達,反而要讓韓淵越俎代庖?
白皎然垂下視線。他不太想與韓淵對視。他輕聲道,
“這次我替你擔保,讓徐將軍出兵了。但是兵權終究在徐將軍手中,若是你向太異常,就算我出面也調不的。韓淵,你說實話,你想讓他們去做什麼?”
“城外再往西走幾個時辰,有一個山谷。白皎然,你知道那里嗎?”
“沒聽說過。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麼?”
“確實沒什麼人。”
“你去那里做什麼?”
“我說了,陛下在那邊等我們。”
“陛下?”
白皎然聲音更加艱了。他猶豫片刻,突然下了決心。他站起來,一把握住韓淵的袖子,
“韓淵,不管你打算做什麼,你收手吧。”
“什麼意思?白皎然,這是陛下的大事,是要去救命的!你可知陛下遇到了危險,不然我也不會找你出兵……我難道不知道出兵需要擔風險麼?說句實話,若不是你在這里,我也不敢想這個辦法
Advertisement
這話說出來,白皎然心中更不是滋味。他眼神從韓淵袍上掠過去。只看這一行頭,似乎韓淵在外面的日子,過得很不好。
“韓淵,你還記得麼?當初我們在酒樓門口初遇時……”
白皎然突然打住了話頭。
“你究竟是遇到了什麼事?若你想走,等會我尋個機會,給你備一匹快馬——現在已經出了平谷關,你去哪里都行,不會被抓到的!若你是缺錢,你信得過我,就留個地址給我——我現在是宰相了,總能尋個辦法替你張羅些!”
他語氣越來越急,韓淵的眼睛卻越睜越大。聽到后來,韓淵愣了片刻,目順著白皎然眼神向自己上服,又看向自己手中腰牌。
他眉微微挑起,才沖到口邊的也被吞了回去。他再抬起頭時,目深深,藏了許多緒。
“你覺得我在騙你?”
“韓淵……”
“若我真的是鋌而走險,來這里哄騙你白大人出馬——白大人,你猜,我會這麼輕易放棄,拿著你施舍的快馬銀錢離開麼?”
“你必須離開!”
白皎然抓著他的手,神激。
“你也在朝中做過,該知道邊關將士多麼銳!若事敗了,你逃不掉的!還不如現在離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那不行。我說過,我是沖你來的。”
韓淵卻挑一笑,單手上白皎然的臉頰,
“不如,我將你一并劫走,也算沒白來一回。”
白皎然盯著他看了片刻,是言又止。恰在此刻,門外傳來徐將軍的聲音,
“白大人,軍隊集結完畢!往哪里去?”
“往……城西那山谷去。”
徐將軍領命而去。馬車行駛起來,有些顛簸。韓淵在白皎然邊坐下,拽了個坐墊遞給他。白皎然不接,韓淵就塞在他后腰。他手撐在白皎然后,整個人也斜了過來。一張口,正對著白皎然的耳垂。
Advertisement
“你到底是真以為我是個亡命徒,還是與我開玩笑的?”
“我希你不是那種人。”
“所以你竟是當真的?”韓淵了下,“那你方才為什麼不那個徐將軍進來,救你出去?”
白皎然垂下頭。他輕聲道,
“韓淵,你真不知道邊關兵士隨都配箭嗎?他們最擅長點殺敵人,若我求救,只怕一支冷箭就會直接取了你命。”
“……”
韓淵揚了揚眉。
“這件事我還真不知道。若不是你口下留,我這一次還真是玩砸了……幸好幸好,皎然你不舍得對付我。不然我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他絮絮叨叨,還帶了些笑意。白皎然眉頭卻越蹙越。他終于忍不住了。
“韓淵,你告訴我,你究竟要做什麼?”
“我方才不是告訴你了……”
“你別敷衍我!”
“哪里敷衍你?我說過了,若是你要趕我走,那我可得連你一起帶走。不然我不干的。”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帶我走?是不是覺得我這個宰相份,方便做個人質?”
“……”
韓淵臉上的笑意不見了。
“白皎然,你這話說得過了。我韓淵會用你來做人質?”
“不然呢?你留下我,想要做什麼?韓淵,無論是走投無路,還是破產躲債,我都可以幫你!你卻不要做些不該做的事——這是將軍府的人,是大燕的銳軍隊!惹了他們,誰能保得下你?”
白皎是突然想到另一個可能,臉瞬間白了。
“你總不會……總不會與些不該接的人勾結在了一起吧?!”
“不該接的人?說說看,什麼不該接的人?”
“西蠻人,或者叛軍……韓淵,只要你不是跟他們勾搭一,我都能保你。可若是你接了他們,那……那我只能盡力幫你逃走,卻不可能眼看你叛國……”
“我明白了。”
韓淵突然打斷了他的話。他后撤了子,距離白皎然遠了許多。那一雙眼睛再沒有笑意,只是冷冷盯著白皎然的臉。
“你的意思是,你覺得我是個廢。你懷疑我離開京城三年,混得連自己都養不活,居然要靠叛國才能求生;你還覺得我是個畜生,一別三年不來找你,三年后來找你就為了利用你!圖你的錢,圖你的權,還想綁架你做個人質?”
“不……若你不是別無他法,也不會……”
“得了,白皎然!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不會說謊?你心里的想法,都他娘的寫在臉上了!看不起老子是不是?老子會把鬼主意打到你上?老子在你心里,原來就是這種貨!”
韓淵頓了一頓。他眼神帶著寒意,白皎然心里也發涼了。
“果然是人靠裝。是不是我今日穿一綾羅綢緞來見你,你就不會這樣想了?當年的白皎然卻不會為這種外所迷,今日的白皎然……不,堂堂大燕的宰相大人,我哪里配你名諱?我該尊稱你一聲白大人吧?”
“韓淵!”
白皎然眼睛里生了霧氣,幾乎咬出來。可是第一次,韓淵見他生氣,卻沒有一點退讓的意思,反而神更加冰冷。
白皎然見他這樣,心中也冷了半截。他沖口而出,
“你說什麼當年的白皎然……當年的白皎然有什麼好?不會被外所,可一樣會被人心所!……若不然,怎麼會與你認識那麼多年,竟然都不知道你有個相好!好到可以丟下陛下派的差事不管,好到可以進了天牢,都不肯吐他份分毫!你怨我不信你,可我依然徐浩然出了兵!你呢?你若是真的將我當回事,這三年里你去了哪里?今日之前,我連你死活都不知!”
話音落地,兩人都愣了。
韓淵的手本來已經進懷里,攥住了李廣寧的旨。此刻,他卻停下作。他眼看著白皎然的角一點點撇了下去,眼角也有了泛紅的趨勢。
韓淵將旨塞了回去。
——這事可是你自己提的,小王八蛋。
——反正軍隊已經往山谷去了,路上還要走上幾個時辰。陛下那點子事,早點說晚點說也都差不多。所以,咱們先把三年前的帳好好算算……
——相好?嗯?原來你這小王八蛋的小腦袋瓜,三年里都在介意這個?!
——老子這些年惦記的相好就你一個……惦記了不知道幾個三年!結果到現在還沒吃到!擇日不如撞日,今天不把你變老子的相好,老子的韓字,就他娘的倒著寫!
……
山谷。
李廣寧懷中抱著杜玉章,靜靜躺在床榻上。他看著房間里的蠟燭從長變短,燭淚一點點淌下來。火也由明亮,漸漸變弱,最后消失在濃郁的夜中。
這一夜,李廣寧沒有,也沒有說話。他覺得心中滿滿都是平靜。他曾經將最珍貴的人弄丟了,曾滿心絕,以為自己再也沒有資格將他抱在懷中……
可今夜,他的玉章,用從不曾磨滅的深沉的意,赦免了他的罪過。
夜中,他低下頭。他能看到杜玉章的臉龐廓突出,就算屋子里這麼暗,也瘦得人心疼。
他的手輕輕在杜玉章臉頰下。懷中人微微一,沒有睜開眼。但是一只涼的手卻按住了李廣寧的手。
“原來陛下也沒睡。”
——陛下。李廣寧心中一陣刺痛。但他不敢奢杜玉章現在還肯他一聲“寧哥哥”,只盼日子長久后,還能捂暖杜玉章那涼的心腸。所以他只是握住杜玉章的手,放在邊輕輕吻著。
“我舍不得睡。玉章,我許久沒有沒有抱到你了……”
杜玉章一陣沉默,輕聲嘆了口氣。
“陛下,你說謊。之前在湖邊那一晚,你明明……你以為我不知道麼?”
“……”
李廣寧一愣。他突然反應過來杜玉章所指——湖邊那一夜,杜玉章陷噩夢。他不自抱著杜玉章整整一夜,又在清晨離開……
“咳咳!”
李廣寧臉紅了。
“那一晚你不是睡著了嗎?你怎麼會知道!”
“我中間醒來過。”
“這……我只是發現你做了噩夢……見你害怕,我想哄哄你而已!我不是有意趁你睡著了,就去占你便宜……”
“我明白。陛下抱著我,我心里確實安穩多了。那一晚睡得很好。”
“那就好。”
李廣寧欣了片刻,突然覺得有點不對——
“等一下。玉章,你是說,那一夜你發現我抱著你,卻沒有聲張,任憑我抱了?”
“……嗯。”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寧公子’啊!才與你認識沒多久的陌生男人,你怎麼能……怎麼能……”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