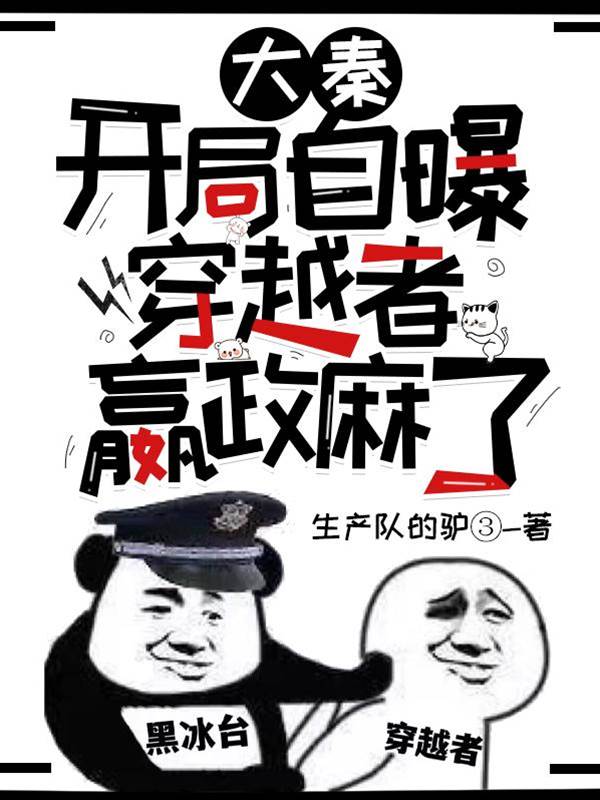《大藥天香》 41、第41章
祖父屋子裡燈火通明,門也開著,繡春進去,見他正立在桌邊,低頭看東西。略掃一眼,果然,就是那個魏王留下的那幅字。便咳了一聲,擡步了進去,笑道:“爺爺,這麼晚了,還不歇?”
陳振朝招招手,等到了近旁,指著那個壽字道:“魏王這樣的人,才真真魏晉風流,風采著實人折服。你瞧這字……”
繡春看了一眼,撇了下,“還湊合吧。這字的好壞,也是隨人份的。他那隻手寫出來的,便是再醜,人家瞧了,也會贊聲好的。”
陳振不以爲然誒了一聲,搖頭道:“這你就不會看了吧。這個字兒,寫得確實好。筆法剛健,又見清逸……”
“行啦,我承認他寫得好,還專門寫給您的,這樣您總得意了吧?”繡春笑瞇瞇打斷了他,“我來,做什麼啊?”
陳振這才從那幅字上擡起眼,坐回到了邊上的一張柞榛木直背椅上,端了茶盞喝一口,“倒也沒啥,就是說說今晚的事。這魏王殿下過來,雖是咱們先前沒料想到的,只也算有過淵源,不算十分突兀。季家的季天鵬竟也會派劉東來送壽禮,你怎麼想的?”
繡春漸漸便收了笑臉兒,坐到了老爺子對面,開口道:“爺爺您說,我聽著。”
陳振看一眼,帶點花白的眉微微跳了下,“陳季兩家,從前不但沒有往來,甚至還有明面上的衝突。剛前些時日,定州那邊出的事還沒徹底平下去,這會兒季天鵬卻差了人來示好。這禮,我收得扎手啊!”
繡春哼了聲,“何止扎手,他今晚演了這麼一出,您等著吧,沒幾天,人人就都知道了,是咱們陳家生就了二兩小肚腸解不開,把季家當敵手防著,人季家卻寬宏著呢,主上門求和。既噁心了咱們一把,往自己臉上金不說,往後要是再出個什麼事,理還沒論,咱們先就輸了幾分人氣!他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
Advertisement
陳振眉頭漸漸蹙,手上的茶盞蓋慢慢旋,“方纔送客之時,我瞧了個機會,朝衙門裡的展老爺打聽了下牢中陳立仁的消息。說他老子先前雖一口認下了所有的罪,只人證確鑿,兒子也是逃不了的。這兩日已經下了斬決,只等上報刑部,下發行文後便可結案……”他看向了繡春,“你既看到季天鵬與陳立仁私下往來,想必他們從前必定有過作。如今事發,咱們沒有舉出季天鵬,是因除了你見了一眼,再無旁的佐證,朝小酒館的跑堂打探,也是茫然不知當時何人。倘若貿然指他,不但不,反會被定以誣告。但陳家這倆父子卻不同,一個已自裁,另個眼見也沒多活頭了,卻始終咬得,一個字也不提。這其中恐怕沒這麼簡單。”
陳振說的,繡春也是想過,道:“我聽說,季家從前曾費過不心力想要竊得金藥譜。他們謀的,可能便是這事?”
陳振道:“藥綱是咱們金藥堂的立命之本。咱們長久以來,之所以能他們一頭,靠的就是藥。你的所想不無道理……”他沉片刻,忽然展眉道:“今日季天鵬不過送來兩挑賀禮而已,倒把咱們弄得這麼惶惶。倘若他知道,豈不正投下懷?他季家如今雖後頭有人,但往後咱們多加小心,做好自己的事,靜觀其變。無事,以不變應萬變,有事,則隨機應變便是。”
繡春微微一笑,點了下頭。
陳振看一眼,“我聽你姑父說,前些日你在藥廠做得不錯,不懼苦累,這很好。明日起,無事再多多過去,多留意裡頭老師傅老把式是怎麼幹活的。這做藥啊,我跟你說,別看就那麼點事,門道可不呢。”
Advertisement
陳振這話,繡春確實認同。恰前幾日,逢春秋二季配製兔腦丸的春時,見幾十名藥工往野兔上拴了繩,牽著在個大院子裡來回奔跑,跑了至兩刻鐘,這纔將兔收攏,迅速砍頭理。當時有些不解,便詢問負責的師傅。經他解釋,這才曉得,這樣來回奔跑過後的兔子頭部充盈活,兔腦中的激素得以充分發揮,用來配藥作產婦催生之用,更有效果。乍聽有些玄,細思之,卻也不無道理。故此刻聽陳振這樣教訓自己,便點頭稱是:“我曉得了。我要學的地方確實還有很多。”
陳振滿意於的態度,端詳片刻,忽然嘆了口氣,道:“繡春,我掌了金藥堂大半輩子,何嘗不曉得這是樁艱難事?讓你一個兒家來守竈,更是難上加難。只是爺爺也沒法子。這是陳家的家業,必定要有人接手下去的,你不會怪我今晚自作主張,強行推你出去吧?”
繡春默然片刻,終於道:“倘若我能,我盡力。”
短短幾字,陳振卻似聽到了莫大妙音,目中閃過一欣之,點頭道:“你肯這麼說,我便放心了。咱們陳家是商家,卻又與普通商家不同。要謀利,更要顧義。不敢說濟世救人,卻必須汲汲小心,因咱們所造之,關乎百姓,人命大於天,須時刻牢記正義明道,以信立本。這話,你可聽懂了?”
繡春起到了他面前站定,恭敬地道:“孫聽懂了,也記住了!”
陳振微笑點頭,俄而,嘆息了一聲:“每一個金藥堂的接承人,從上輩那裡得到的第一段教訓就是這個。想當年,我也曾對你伯父、你爹教導過這段話……”
他的聲音漸漸消了下去,神轉爲慘淡。
繡春下心中的難過,忽然道:“爺爺你稍等。”轉飛快跑了出去,很快,回來時,手上已經多了雙嶄新的黑麪白底布鞋,在陳振驚詫的目注視之下,遞到了他面前,微笑道:“幾天前才曉得您今日過壽,一時也準備不好別的禮,我又笨,只會做鞋。所以趕著做了一雙,當做孫的壽禮。”
陳振接過,雙手竟微微抖,只不住點頭,道:“好,好……”再無別話。
這布鞋,是繡春前頭幾天,悄悄量了他的舊鞋尺寸,然後趁空連夜趕著做出來的。此刻見祖父這欣喜樣子,想起當初自己給父親穿鞋時的一幕,不也是黯然。
陳振小心地放下鞋子,擡手不經意般地掠了下眼角,看向繡春時,面上已然含笑,道:“不早了,你去歇了吧。明日起,爺爺便要人把咱們家門檻的鐵皮再包一層了。”見繡春不解的樣子,呵呵笑了,“不多包一層,恐怕就要被求親的人踏破了。”
繡春這才明白,自己是被老爺子打趣了,也不忸怩,只嘻嘻一笑,朝他扮了個鬼臉,“爺爺你也早睡。”告退而出。
~~
蕭瑯回了王府,比平時要早些,徑自去書房,稍晚,方姑姑親自送了宵夜來,看了眼他,疑道:“方纔金藥堂的人來了,送了十瓶子的紫金膏。是你親自去金藥堂要的?”
蕭瑯視線仍落在手中的書上,一笑。
方姑姑見他默認,忍不住再問,“殿下怎的會去要那麼多藥膏過來?”
“今日出宮早,所以順道。”蕭瑯隨口應道。
方姑姑更訝了,“剛前日,陳家不是打發了人送來兩瓶新制的了嗎?蔣太醫說估能用一個月。我下回叮囑他們,不必一次送這麼多瓶來。因時日擱久了,藥效怕有失。這一下又來了十瓶子,當飯吃也夠幾天飽了。”
蕭瑯一頓,終於擡起了眼皮。
呃,怪不得自己先前開口後,陳家老爺子和邊上那個看似管家的人面上仿似有過一陣微微錯愕表,原來是這個緣故……
“送來就送來了,放著吧。”
他了下鼻子,淡淡道了一句,繼續看書。
方姑姑瞥他一眼,忍住笑,“你不顧份去闖人家的壽筵,會不會嚇到別人?都見著了些什麼人?”
蕭瑯眼前再次閃過那一幕,他第一眼看到兒裝扮的立在那裡,半側著臉,與自己兩兩相。他是被驚豔了,卻顯見是被他給驚住了。周遭的一切聲和人,彷彿都了他們的陪襯……
這種覺……
“殿下,殿下?”耳邊傳來方姑姑的聲,蕭瑯回過了神。
“殿下,在想什麼呢?”方姑姑搖了搖頭。
蕭瑯略帶不好意思地一笑,“沒什麼。”
方姑姑看他一眼,再次搖頭,“我曉得了。夜裡還冷,你別熬得太晚。先前那個陳家娃娃也說過,你要多休息,尤其不可熬夜。”
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最後提了下繡春。
蕭瑯點頭道:“曉得。姑姑也早些睡。”
方姑姑第三次搖頭,徑自去了。
這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在一旁都有些心急了。
~~
半夜時分,一個人影被推上了馬車後廂,馬車迅速啓,消失在了夜半的黑暗之中。
陳立仁從麻袋裡被放出來時,四顧,見是荒野。邊上立了個人。接了晦暗的月,看清正是季天鵬,頓時跪坐在了地上,低聲道:“我半句沒提到你!”
季天鵬厭惡地瞟了他一眼。這個剛從死牢裡被置換出來的人,蓬頭散發,全髒污,散著一惡臭之味。
“我知道。否則你怎麼會在這裡?明日會有人代替你去死的。”
他冷冷道。
陳立仁手腳發,卻強自撐著道:“當家的,我之所以會落到今日地步,跟你也是不了干係的。要不是你設局害我欠下大筆賭債,我在金藥堂好好的,怎會做出那樣的事……”
季天鵬呵呵笑了起來,呸了一聲,“是你自己沒用,怪我做什麼?我捆你進賭場了?”
陳立仁道:“是,前頭這些就不提了。只說陳家老二的事。要不是被你著,我怎會人去燒了他?要不是有這事,我如今還過得好好的……”
“滾你孃的蛋!”季天鵬打斷了他,冷笑道,“你父子倆難道就不想讓他死?他要是不死,陳老頭子怎麼可能會把金藥堂給你們?我只你們把藥綱給我弄來。可沒你們放火去燒他!”
“好……好……都是我自己的錯!”陳立仁破罐子破摔,索無賴起來,“這些年我雖從金藥堂里弄了不錢,只大多都拿去清了賭債。我家的婆娘孩子也已回了鄉下老家,如今我啥都沒了,你要不幫我一把,天理也說不過去!”
季天鵬輕蔑地道:“老子既把你弄出了死牢,自然不會讓你死。”噗一聲,往他跟前丟了袋銀子,“這些你拿去。老家也不要去了,給我尋個地方好好藏起來,機靈點不要頭。”他頓了下,“你放心,等我拿到藥綱,金藥堂也垮了的那一天,我一定會讓你重新回去掌管的!”
陳立仁明白了過來,“你留下我,是覺著我還有用。陳家人才知道陳家事是吧?”他手拿過錢袋,掂量了下,“太了。再給點。”
季天鵬皺眉,手從懷裡再掏出兩張銀票,投到了他臉上:“等著我消息!”
~~
早春在一日日的晴好天氣裡很快到來了,萬復甦,上的厚重冬也漸漸去,到是一派生機的景象。
陳振壽日後的這個月,陳家幾乎沒別的什麼事,只顧應付登門而來的人說客了。隔個一兩天,便有人登門問親。正所謂好百家求,何況是金藥堂陳家的獨生嫡親孫?正當二八妙齡,人又生得如花朵兒一般,有人慕求娶,那也是理之中。陳振頗興趣,親自認真接待人說客。只他眼高於頂,這般看下來,到最後竟覺沒一個能眼的,只覺自己孫是天上仙,凡間簡直沒一個男子能配得上。漸漸的,不知道哪裡傳出去的消息,說陳家的孫要守竈,不嫁人,只招贅,立刻擋住了一大撥人的腳步,門庭漸漸這才冷落了下去。這日,等著繡春從宮中回來,陳振了到跟前,瞪著眼問道:“我聽說,是你自己人放出的話?說要招贅上門?”
這話確實是繡春放出去的。實在是前段時日,來求親的人太多,本還無意嫁人,不勝煩擾,乾脆便使出了這招殺手鐗。
這世代,即便窮得叮噹響,連個飽腹也混不上的男子,也絕不會輕易想著去當上門婿。丟不起那個臉。
“是啊,”繡春乾脆承認,“您不是要我接您的事?我往後不招贅,要是嫁了人隨了夫姓,還怎麼守您的家業?”
這個問題,陳振自然早就考慮過。他也不得不承認,只有招贅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只他也清楚,招贅恐怕難招到勘配自己孫的男子,故而這段時日一直於矛盾緒之中。此時見繡春這麼幹脆承認,盯了半晌,一時說不出話。
繡春笑道:“在我跟前,您就別裝了!我估著哪天就算我想著要嫁人,你也會千方百計不讓我嫁,除非那男人肯贅咱家。我還不知道您的心思?”
陳振被破心思,頓時一陣老臉發熱,咬牙盯著繡春,“沒大沒小!有這樣跟爺爺說話的嗎?”
“是是!”繡春忙作出害怕模樣,“是我不好,想錯了您!爺爺您大**量,千萬別見怪!”
陳振無奈搖頭,忽然想起件事,問道:“明日要去城外西山莊子裡採鹿茸,準備好了沒?”
陳家的蔘茸生意是個大項。諸多鹿茸中,以梅花鹿爲上品,又以野生鹿之鹿茸爲頂級貨。只是鹿兒生機敏,獵戶野外捕捉採茸並非易事,所得鹿茸有限,故而陳家在城外西山莊子裡便有個馴鹿場,裡頭養了數百頭的梅花鹿。每年採兩次鹿茸。所得鹿茸,與野生鹿茸分級售賣,質量最好靠頂的,稱片,中段切下來的稱蠟片,靠近基部的一段,則稱片,價格也相對便宜。明日由朱八叔帶著便要過去。繡春也跟去。聽祖父問這個事,忙停了玩笑,道:“是,都準備好了。”
“你朱八叔是高手,好好跟他學著。”
“是,曉得了。”
繡春應道。
猜你喜歡
-
完結942 章
獨步逍遙
貪戀紅塵者,不求成仙,不求成佛。 隻求世間繁華,你我安好。 但若天地不仁,神佛貪婪。 我唯有怒而提劍,斬出一個浩瀚宇宙,可獨步之,逍遙諸天。 …
87.9萬字8 6516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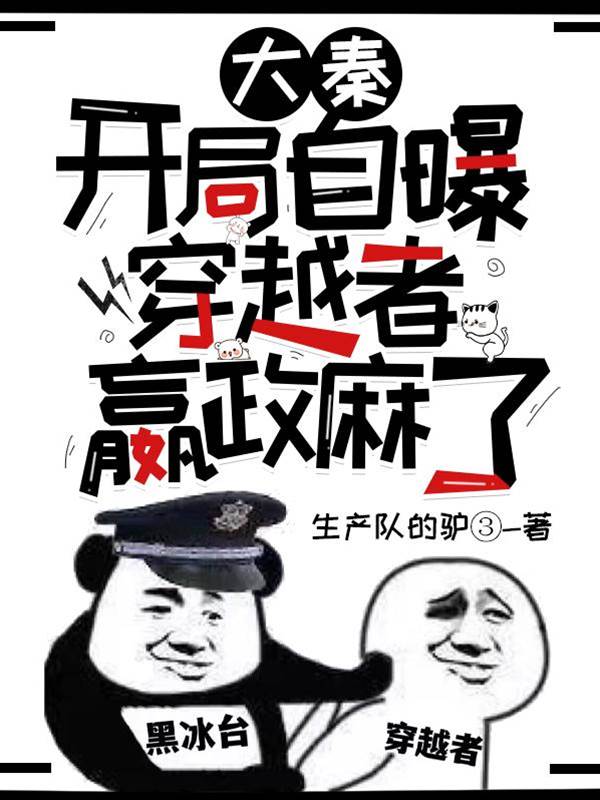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