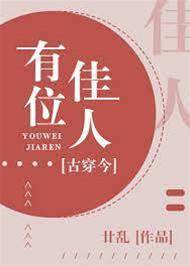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尋秦記》 第12章 兵行顯著
二十七個敵人,被他以出其不意的戰,放倒九個,其他人則被嚇破了膽,四散躲避,再沒有先前的銳氣。項龍知目的已達,凌空翻到更遠的樹上,敏捷的回到地上,迅速朝早先敵人馬蹄聲歇止的方向奔去。
只兩刻多的時間,他終抵達林外,近五十多頭戰馬系在林外徜徉。這時已是夜半,明月高掛,大地瀰漫著森幽神的氣氛。項龍揀取其中一匹健馬,斬斷其他馬兒的系索,再將馬兒一匹匹的系在一起,以浪輕馬,馬兒痛嘶聲中,你牽我扯的整羣走了。
項龍跳上挑選的戰馬,好一會才控制得它驚的緒,放蹄而去。三天後他無驚無險的越過草原,棄馬進魏韓界的邊區,心至此大是不同,竟然頗有點遊山玩水的意味。此時中牟只在正北百里許外,項龍鬚有很大的自制力,止直接投奔中牟的強烈慾,那當然是最不智的魯莽行爲。
天氣漸轉寒冷,幸荊年爲他備有冬,使他不用捱冷苦。走了五天,他抵達毗連山區的外沿區域。旭日初昇中,灑在山區外的原野上,在草樹間點染金黃,呈現一片生機無窮的氣象。不遠有座大湖,當寒風吹過,水紋盪漾,岸旁樹木的倒影變化出五彩繽紛和扭曲了的圖案,看得項龍更是心曠神怡,渾忘逃亡之苦。叢莽的原始森林和茂的灌木、延展無盡的草地和沼澤中的野生植,把如若一面明鏡的大湖圍在其中,實是人間勝景。湖旁的草地上豎起十多個帳幕,還有羣的馬羊,正在草原間悠閒地吃草,氣氛寧洽。
項龍觀看好一會,收拾心,朝大梁的方向進發。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的往大梁奔去,而是準備到達大梁的郊野後,循以前由趙往大梁的舊路返回趙境。雖然要繞個大圈,卻是他可以想出來最安全和悉的路線。
Advertisement
一個時辰後,他已深魏境的草原。想起當晚遇伏,由疾風揹著他落荒逃走,最跑近三百里的路程,從他現在的位置沿此奔至趙魏兩國界,再繞到邇近荊家村山區的山野,力竭倒斃。目下他是重回舊地。
往東北走近三個時辰,蹄聲在前方響起,項龍忙躲起來,不片刻一隊約二十人的魏兵,直馳而至,到了附近一高丘上,竟紮營放哨。項龍看得頭皮發麻,心不妙。魏人顯是收到風聲,知他或已逃來此。要知由這裡無論朝中牟或大梁的方向走去,都是平原之地,所以悉自己國境的魏人,只要在地勢較高設置哨崗,他若稍一疏忽,便顯行藏,難逃被發現的後患。敵人顯然仍在著手佈置的初期階段,一俟設妥哨崗,會對整個平原展開水銀瀉地式的搜索,在快馬加上獵犬搜弋下,自己休想有逃生的機會。最要命是抵達大梁之前有幾條擋路的大河,魏人只要配備獵犬,沿河放哨,縱是晚上,自己恐仍未可潛過河道。
想歸這麼想,但除非掉頭回到山區,否則只好繼續前進。現時無論折返韓境,又或南下楚域,危險並不會因而減。問題是應否把心一橫,直接北上中牟,那至多兩天時間,可以回去與滕荊兩人會合。這想法比早前有更驚人的力,而那亦是最危險的路線。
直至太西下,項龍仍在該往何去的問題上進行著激烈的心鬥爭。最後終於把心一橫,決定先往中牟的道路試探,假設確沒有方法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改爲東行折往大梁,依原定的計劃趙返秦。下了決定,反輕鬆起來,多費半個時辰繞過敵人的哨崗,北上中牟。在到達中牟之前,尚要經魏國另一大城“焦城”。他當然不會有城的打算,還得格外留神,免給魏人在那裡的守軍發現。
Advertisement
以特種部隊的敏捷手,天明前他走了近三十里路,跑得部酸了,最後躲到一林休息。他還不放心,費了點工夫爬到一棵大樹枝葉濃,半臥在橫丫上,閉目假寐。這棵大樹長在地勢較高和林的邊沿,可俯瞰外面的平野和通往焦城的大道,不半晌便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蹄音和人聲把他吵醒過來。
項龍睜眼一看,大吃一驚,林林外俱是魏兵,說也有千人之衆,正展開對這一帶的搜索。立時汗流浹背,知自己因過度疲勞,直至敵人來到下方纔醒覺,若非睡是在三條樹幹形的凹位,說不定早在酣睡中掉到樹下去。他指頭不敢半個,直到魏兵在樹下經過,始敢探頭觀察形勢。林外的道先後馳過兩隊騎兵,更遠一座高丘上另有人馬,似乎是這次搜索行的指揮部。看敵人這種規模,便知自己曾對他有恩的魏王增已下了不惜一切,也要把他擒殺的命令。這批至有二千人的部隊,很大可能是來自焦城的駐軍,且只是整個搜索隊伍的一部份。以這樣的兵力和魏人對自己國土的悉,他如今確是寸步難行。不頗後悔,假若不是因歸心似箭,想往中牟,而是繞道往大梁,便不至陷如此危險境地。眼下最明智的做法,莫如折返韓境的山區,躲他十天半月,待風頭過後,那時無論逃往何,都會容易多了。
犬吠聲此時在林某響起,項龍更是頭皮發麻,只能聽天由命。這一刻由於人多氣雜,他還不太擔心會給獵犬靈敏的鼻子發現,但若在晚間單獨奔走,又是夜深人靜,便難以保證能否避過犬兒的耳目。見到敵人的陣仗,他哪還敢往焦城去,待邏卒過盡,由北上改爲東行,朝南方大梁潛去。施盡渾解數,避過重重追兵,這晚來到著名大河“賈魯河”的西岸。
驟眼看去,兩岸一片平靜,不見人蹤,但項龍可以肯定必有敵人的暗哨,設置在某林之,監視河道的靜。他細心地觀察,假設了十多個敵人可能藏的地方,然後躲往樹上去,靜待黑夜的來臨。
疲累下很快即睡,醒來時天地化作一個純的白世界,臉上上雖沾有雪花,卻並不到寒冷,初雪終於降臨。項龍撥掉上的雪,心怔忡的看著仍灑個不休的雪花。
風雪雖可掩蔽行藏,卻不宜逃亡,若此時跳進水中,又溼淋淋的由河裡爬出來,說不定可把他活生生凍死。而且雪停時留下的足跡,更難瞞過敵人的追躡。目下他只有三個選擇,首無是砍木作筏,好橫渡大河。不過此法既費時失事,又非常危險,徐非他肯定敵人崗哨的位置不在附近,否則若驚敵人,那時在河心本沒有手頑抗的機會。其次是沿河往上游奔去,依荊年的地圖,此河源頭起自中牟西南方的山區,不過若這樣做,繞過河頭時已非常接近中牟南郊這極度危險的區域。且若要再往大梁去,路程將比早先定下的路線遠了近五百里,並不劃算。
剩下的方法是朝下游走,那樣雖離大梁愈來愈遠,卻較易離開險境。若到達下游位於數條大河匯的安陵,既可找尋機會乘船渡河,甚或可改道南下楚境,即使給楚人逮著,說不定李嫣嫣和李園肯念點舊,把他釋放。
下了決定,遂匆匆上路,沿河南下。走到天明,大雪終於停下。項龍回頭一看,只見足跡像長長的尾般拖在後方的雪原上,不由暗暗苦。再走一段路,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會給追兵發現,靈機一,停了下來,先視察形勢,定下計劃,忙朝附近一片樹林趕去。林後拔出浪,劈下了一株選的榴樹,再以匕首削兩條長達五尺的雪板,板頭依足規矩翹起許,中間偏往板尾亦前後高起許,剛好可把自己連靴的腳板踏進去,爲固定的裝置。又鑽出四個小孔,把勾索割下兩截,穿孔而過,可把鞋頭和樹板綁束穩妥。最妙是在板底刮出一道貫通頭尾的導向槽,一切似模似樣。到黃昏時,中國的第一對雪板終於面世。
項龍在二十一世紀當特種部隊時曾過良的雪訓練,此時自可駕輕就。完雪板,接著是製造雪杖。雪杖頭寬尾尖,近尖端三寸許,扎有一橫枝,充作“雪”。
一切妥當,已是夜深。由於削割堅如鐵的榴木,花了他大量氣力,休息了一會,然後展開行。他把板雪杖掛到背上,徒步朝河岸跑去。雖仍是舉步維艱,但心和先前已有天淵之別。近天明時,他走了足有三里路,至大河岸邊而止。還故意攀到水緣,留下清晰的足跡,才倒後踏著原先的足印,回到河岸上去。然後穿上板,綁紮妥當,一聲呼嘯,開始雪壯舉。
他利用起伏不平的地勢形的斜坡,不住加速,由緩而快,繞了個大圈子,兩耳生風的回到剛纔的林,然後藏在一棵高出附近林木的大樹頂。只覺神無比,要經好一段時間,才能靜下心來閉目假寐。到了正午時分,敵人終於來了。項龍聞聲睜目一看,大吃一驚。只見漫山遍野全是魏國騎兵,說也有過千之衆。他們沿著他留下的清晰足跡,朝樹林全速奔來。項龍看著他們穿過樹林,往河岸追去,到了他足跡終止,倏然停下來商議。不一會魏兵紛紛下馬,伐木造筏,忙個不休。
這時又下起雪來,比上一趟更大。一球球的雪團似緩似快的由灰黯的天空降下來,只片晌掩蓋了原先留下的蹄印足跡。項龍暗天助我也,如此一來,當敵人在對岸再發現不到他足跡,勢將分散搜索,愈追離他愈遠。大雪本對他最是不利,現在反爲他的護符。
正心中欣然,犬吠聲在遠方響起。一隊百多人的徒步魏兵,拖著十多頭獵犬,沿河而至。項龍心中恍然,知道這隊伍與正在岸旁造筏的騎兵隊本是一隊,但因馬快,又發現他留在雪地上的足印,匆匆趕過去,所以獵犬隊伍落後近一個時辰。不暗好險,若剛纔先到的是這隊獵犬隊,自己的妙計可能不靈,現在只憑大雪已足可沖掉自己的所有氣味。待至黃昏,魏人全渡過大河。項龍又耐心靜待兩個時辰,爬下樹來,趁著月黑風高、雪花漫天的良機,掣起雪杖,鳥兒般在漫無止境的雪地飛翔,掉頭朝賈魯河馳去。有了“雪地飛行”的工,他決定冒點險往中牟,逃亡至今,他首次對前途充滿希。
項龍伏在草叢,細察敵人的營帳。只兩天工夫,他便完平常最要走十天的路程,直抵中牟南方十里許的趙軍軍營。他原本頗有信心過敵人的防線,潛往中牟。可是當見到實際的況,夢已像泡沫般抵不住現實的而破滅。最頭痛是李牧把附近一帶能提供遮掩的林全砍掉了,又在向著他這方面的平原挖掘長長的陷坑,通道均有人把守。縱使他可通過陷坑,還須經過三重柵寨,方可進趙營。何況縱能潛過連綿數十里的營帳,還有中牟外一片全無掩蔽的廣闊平原。以李牧的佈置,是絕不容許任何人往來中牟。現在的他,像得半瘋的貓兒,見到味可口近在咫尺的魚兒,偏是吃不進肚子去,那種痛苦,難以形容。唯一令他到欣的是李牧雖把中牟圍得水泄不通,顯然仍對中牟這堅城毫無攻破的良方。他最清楚中牟的況,守上個一年半載,絕非難事。
現在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照原定計劃回到大梁去,再潛往趙境,由那裡返屯留與桓齮會合。另一方法是繞越中牟,再過趙人的邊防,逕回秦國去。後一選擇當然危險多了,以李牧的算無策,必在邊境廣設哨站,防止秦國援軍東來。若他沒有雪板,這樣做只等於自投羅網,但現下卻非沒有功的機會。慾像烈焰般燃燒著他的心,一陣蹄音犬吠聲,由西南方傳來。項龍的心直沉下去,就在此刻,他放棄人的想法,爬了起來,朝大梁的方向逃去。
翌日黃昏,他到達魏都大梁城的郊野。重回舊地,想起已作古人的信陵君魏無忌,不百集。此時他早吃盡乾糧,既飢且累。而大梁城的防明顯地加強,所有制高點均設有崗哨,最令他泄氣的是攔路的幾條大河和人工築的河。
觀察一會,他知道必須先渡河到大梁,然後再越過大梁另一邊的河方能奔赴趙境。這樣便得先購買足夠的糧食帶在邊,因際此天寒地凍之時,再不能像以前般可摘取野果充飢。他目前最大的優勢,是魏人並不知他到了這裡來。所以要越過大梁奔赴趙境,並非不可能辦到的事。打定主意,他先把雪板、雪杖、弩弓等找一地點埋下,立了標誌記認,才爬上一棵大樹,掃掉積雪,在樹丫瑟一團,苦候天明的來臨。到午夜時分,雨雪紛紛的從天而降,冷得他直髮抖。飢寒迫下,他只好咬牙苦忍。自遇襲逃亡,他一直靠堅強的意志屢次從敵人的羅網中。但現在沒有了敵人步步進的威脅,反而胡思想起來。例如荊年派出的人,是否能通知滕翼等有關他的消息?又假如遠在咸的妻婢們,知道他的況,會有什麼反應?種種憂慮,似如千斤重擔般著他的心頭,令他完全沒法放鬆下來。的痛苦,實遠及不上心靈的負擔。
忽地打兩個寒戰,腦際昏昏沉沉,意識逐漸模糊。再醒來時,渾痠痛,發覺自己已由樹上掉下來,上堆滿雪花。冬早出來了,弱無力的由樹頂灑進林。他好不容易爬起來,只覺臉額火辣辣般燒著,意志接近崩潰的邊緣。他竟在這要命的時刻病倒,項龍只覺無論心靈均是無比的弱,但又知若不繼續行程,到寒夜來臨,他休想有命再見明天的太。
想起妻兒,他勉力站起來,跌跌撞撞,倒下又爬起來的往林邊緣踉蹌而去。勉強來到林木稀疏的邊沿,終支持不住,倒了下來。也不知昏迷了多久,醒過來時,車磨雪地的吵音傳耳際。他睜目一看,林外往大梁的道有一隊騾車隊經過。早消失了,天空烏雲佈,正醞釀另一場大雪。項龍知道此刻正值生死關頭,覷準無人注意,勉力竄出去,趕到其中一輛騾車後,爬上車子,鑽布帳蓋的拖卡去,倒在綿綿似是麥子一類的東西里,然後失去一切意識。
猜你喜歡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57348 -
完結1853 章

蝕骨溺寵,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一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一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襠部支起,她笑瞇瞇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一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慍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襠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換個法子解,本王給你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麼落在她肚子裡了。
346.3萬字8.18 58912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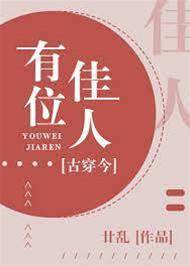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5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20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