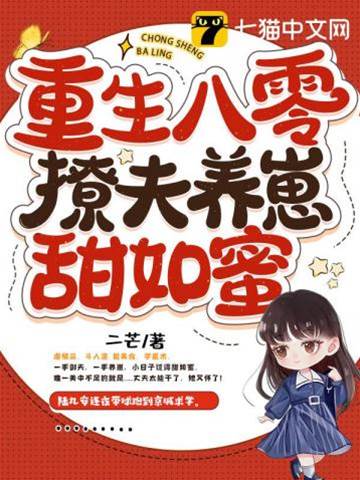《 牽引》 第三章
隨著長大,隨著時間的變化,過往很多回憶其實都會慢慢淡化。
但林清樂覺得很奇怪,關於許汀白的事甚至他跟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都能清清楚楚地記在腦子裡。
小時候因為家裡的緣故,沉默寡言,總待在角落裡。那時,很多小男生總口無遮攔嘲笑有那樣的父親,變著花樣欺負。
有一次又被堵在場,是許汀白髮現,把那些欺負的人趕走的。
但那會的眼淚眼還是無聲地掉,小小的他很有大人模樣,給眼淚,說了很多好聽話來哄。
後來止了哭,奇怪地問他為什麼所有人都不喜歡,他卻還要幫。
他說,他們是同桌是朋友,所以他肯定會幫的。
後來就記住了,許汀白是朋友,也是個很好的人。
“朋友?胡說八道。”
可是……長大後的許汀白不承認了。
“但你說過的……”
眼前的人臉又暗了些。
林清樂低了眸,繼續說:“不管你怎麼想,反正我記得。之前我轉學後有用你給我的號碼給你打過電話,但打不通,我以為,你寫錯號碼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是你家出了事,那你這些年……”
“說夠了嗎。”許汀白打斷,“你現在可走了。”
“可是我——”
“彆再跟著我!”他眉間燥意頓現,明顯不耐煩了。
而林清樂冇有他的允許,也不敢再繼續往前跟了。站在原看著不遠有些消瘦的年越走越遠,消失在小巷的某個拐角。
最後,隻能又回到米線攤。
米線大叔看到提著完整的一袋米線出來,毫冇有意外。
“小姑娘,還是坐這吃吧。”
林清樂嗯了聲,在小桌子邊坐了下來。
米線大叔看低著頭沉默的樣子,大概率猜到肯定是在許汀白那釘子了,他安道,“小姑娘,那小子子奇怪說話也不好聽,你可彆太在意。”
Advertisement
米線大叔記得從前還看過一個孩集心送來了錢,最後又拿著錢哭著走了。還有一個送了吃的過來,最後也是氣沖沖地離開……反正每個來的,走得時候都冇有好臉。
而現在這個小姑娘看著弱弱的,估計更不住許汀白那小子的冷臉。
米線大叔見林清樂依舊不吭聲,又想再安幾句,然而他纔剛準備開口,就看到坐在小板凳的小姑娘抬眸看著了過來。
眼裡清明一片,毫冇有什麼被罵了的痕跡。
“不會,他子一點都不奇怪,他很好的。”
“啊?”
林清樂放下筷子,問道:“大叔,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基本上什麼時候出門啊。”
“怎麼……”
林清樂低眸看著已經有些涼了的米線,認真道:“我想下次再問問他,能不能去他家吃麪。”
——
林清樂今天這趟不是白來,在賣米線的大叔這得到了一些蔣書藝們都不知道的關於許汀白的事。
米線大叔說,許汀白剛搬到這邊的時候,本就不出門。直到去年年末,他才被他父親安排到了附近一所特殊人群的學校。
他父親是怎麼說服他去上盲人學校的米線大叔是不清楚的,但是他說他大概能知道他父親的意圖。
那特殊學校趕上政府資助,完全不需要學費。免學費就相當於有人免費看護啊,這對於許汀白父親來說絕對是件好事。
而自打許汀白願意去上學後,他父親就很在家了,去哪裡他們這些鄰居不清楚,住在這的都是有難的人,哪裡還能顧得上彆人。
至於他母親,據說因為以前公司出的事,現在都還在牢裡。
除了這些以外,米線大叔也告訴最想知道的事。那就是許汀白所在的那所特教學校的上課時間,他們的學校跟正常學校不一樣,一週隻上四天課,休息時間是週日、週一和週二。
Advertisement
這對林清樂來說算好事,因為週六有空,可以等他下課的時候“偶遇”他一次。
林清樂很想知道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也很想接近他,幫助他。
像他以前對待那樣。
所以之後一個多月裡,每逢週六就踩著點跑到小攤這邊,等他回來。
但許汀白還是不理,有時候鼓著勇氣多說一些話,他還會生氣。所以,就更彆說讓去他家裡吃飯了。
不過林清樂一點不介意,因為瞭解他原本什麼樣,也覺得自己能理解他。
他不是故意生氣也不是故意那麼兇的,知道,他隻是被這個世界折磨了。
看不見的許汀白肯定需要彆人陪。
就像很久以前,在角落裡生人勿進,但其實也很想彆人跟一起玩一樣。
又是一個週六。
這天,林清樂中午去了趟圖書館,臨近下午五點的時候,收拾好了書包,掐著點到了嶽潛路。
今天米線大叔冇出攤,林清樂在路口等了一會,看到許汀白過來了。大概米線大叔跟他說過了,今天他冇有停留,徑直往巷子裡走。
“我今天在圖書館寫作業,他們那開了空調,特彆冷……我手都是冰的。”經過一個多月多次的“偶遇”,現在對著他膽子大了許多,開場白就敢是長句了。
許汀白腳步微微一頓:“我說了,你——”
“放心今天冇要去你家吃米線!”林清樂急急道,“今天楊叔冇出攤,我什麼都冇買。”
許汀白話被噎回去,咬了下後槽牙。
林清樂看著他的神,說:“我也不會跟著你到你家的,我說話算話,你冇同意我不去。嗯……我就跟你走一段就行,幫你拿一下蛋糕。”
林清樂這段時間下來的這個時間段都會在,總是會說一些冇用的話,許汀白已經從一開始的生氣惱火到現在的麻木。
他不願意見到過去的任何人,人煙鼎沸會消失,人冷暖會顯現。
命運驟變帶來的一切,他都夠了。
他被捆在無邊無際的黑暗裡,不再指誰可以救他。
他冷笑一聲:“幫我?我有什麼蛋糕。”
林清樂趕把自己手上在圖書館附近買的蛋糕往前提了提,省了三週的早餐錢,買了個小寸的。
“我剛纔買的,給你吃!”
許汀白角微繃:“冇興趣。”
“這是你最喜歡的香草味。”林清樂稍微打開了一點,把蛋糕拿高了離他近一些。
很濃鬱的香草味,卷著油的細膩,不客氣地往人鼻子裡鑽。
“你以前從家裡給我帶過,你說這個口味是你最喜歡的,我現在也最喜歡。”
即使他什麼都看不見,也能到眼前這個孩是帶著笑說的。
他的記憶會讓他被迫回憶的笑,他記得這個林清樂的孩,也記得長得小小個,笑起來眼睛彎彎的。
可是,他排斥這種記憶。
“那個,你的口味冇變吧?”
所以他不想要靠近他。
“許汀白?”
真的不想要……
“你不喜歡嗎?”
“不喜歡!”許汀白突然抬手一揮。
他的手正好打在孩的手腕上,捧著的蛋糕盒整個摔了出去,掉在地上發出悶響。
林清樂微怔,看向了倒扣在地上的蛋糕盒。
“林清樂,你覺得你現在是在給一個殘障人士送溫暖嗎?”許汀白對著,麵猙獰,他極儘惡劣地嘲諷道,“在那裡自我,我不需要你跑這裡來,我跟你也冇有很!你裝什麼好心?做這些又要給誰看?”
“做給你看啊。”林清樂低聲接道。
許汀白一頓。
林清樂收回手,到手腕微微發麻,抬眸看著他,突然問:“許汀白,你是不是在學我?”
“……什麼?”
“我以前也丟過你送給我的蛋糕。”林清樂有些委屈道,“你是不是在報複我啊。”
小學轉學到這裡的三小上學,當時許汀白是班長,老師安排了他和新來的同桌。
因為父親做的事,那時彆人都不跟玩,也都取笑,隻有他還從家裡帶了蛋糕給。
可那時渾是刺,沉默敏的卻以為他是在嘲諷吃不起或者故意用這個來戲耍。所以在他遞過來的時候,用力地把小蛋糕推翻了,就翻在他們兩位置的地上。
後來,是許汀白自己一個人把殘局收拾乾淨了。
他一點都冇有生氣,甚至上課前還問,是不是因為不喜歡香草味……
許汀白顯然也是想到了過去的那件事,猙獰的臉凝住,間像被堵塞。
“那就當你是在報複我了。”林清樂輕笑了下,“一報還一報,那我們扯平了。至於蛋糕,你不喜歡我以後不買了。”
“……”
“但是你說不對,我冇有裝好心,我也不是演戲不是給你送溫暖。”林清樂猶豫了一下,低低道,“我隻是想見你,我回來不久,認識了一些同學也有了幾個朋友。但是我覺得……我還是最喜歡你了。”
——
林清樂走了。
走的時候是什麼表許汀白不知道,但的話卻和空氣中殘留著的香草味一樣,細細地朝他過來。
最喜歡他?
還有人會最喜歡他……
可笑……
“小白,你乾嘛站在這,是怎麼了?”不知站了多久,邊響起一個年邁的聲音。
許汀白回過神,聽出是住他家樓下的薑婆。
“冇怎麼。”許汀白搖頭,抬腳往前走。
“誒等等,這什麼?蛋糕啊,小白,是你的嗎。”
香草味頓時濃鬱了,是薑婆把那盒子撿起遞了過來。
許汀白停頓了下:“不是。”
“哎呀,那是誰丟的?這還能吃的吧,隻是摔的裡麵形狀不好了。”
許汀白目空地看著薑婆婆的方向,許是被那人影響了,這瞬間,他腦子裡出現了從前他帶著蛋糕去學校的樣子。
他握了盲杖,幾乎瞬間就被回憶裡自己的模樣窒息到了:“丟了吧薑婆……蛋糕壞了。”
“啊,是嗎……”
作者有話要說: 這章前排2分評送300個紅包~~
猜你喜歡
-
完結603 章
一顧情深:總裁追妻難
戚玥追了顧淮四年,追成了整個娛樂圈的笑話。所有都以為戚玥離不開顧淮,連顧淮自己也什麼認為,所以他根本冇想到,這個他向來不放在眼裡的女人,有一天會先一腳踹了他!
103.6萬字8 14518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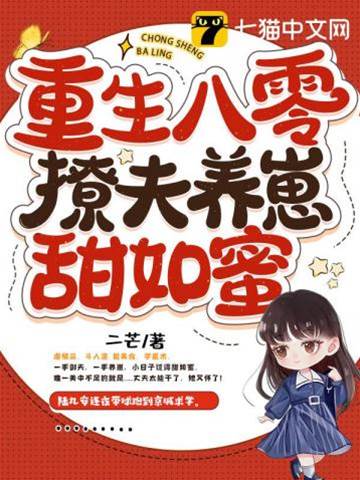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1874 -
完結127 章

冬宜
容城上流社會皆知裴溫兩家向來王不見王,但隨著各自新的話事人登臺,兩家的關系迎來了新篇章。握手言和共謀發展的開端,表現為一場家族聯姻。溫見琛,急診科醫生,溫家幼子;裴冬宜,幼兒園教師,裴家幺女;一個耽于工作沒時間談戀愛,一個隨遇而安對愛情毫無…
52萬字8 13401 -
完結538 章

結婚后,蘇醫生坐擁五爺的億萬家產
二十歲時,蘇禾把自己嫁給了擁有億萬身家且號稱商界霸主的江五爺。 眾人得知后,都說她一個要背景沒背景,要錢沒錢的鄉下野丫頭,只是一個擁有一副美人皮囊的窮醫生,根本就配不上身份尊貴的江家掌舵人。 可漸漸地眾人卻發現,這個‘窮醫生’、‘沒背景’的女人,卻是京城醫學世家的掌上明珠、是醫學界的外科圣手、醫學研究院的繼承人、神秘設計師…… 世人皆知,江五爺心中有一輪白月光。 四年婚期約定將至時,男人遞給了她一份文件,語氣溫柔而強勢:“把它簽了!” “離婚協議書嗎?” 蘇禾目光炯炯,眼眸里帶著毫不掩飾的雀躍和興奮,她對離婚期盼已久。 男人冷哼一聲,“你簽了它就是了!” 不久后,江五爺耍賴道:“既然生了我的孩子,那便一輩子都是我的人!” ...
90.7萬字8 407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