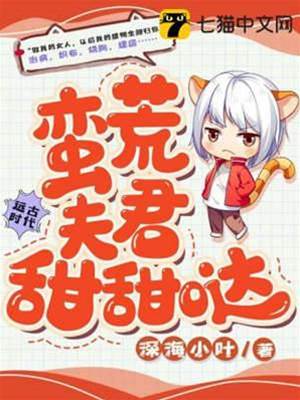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離凰》 第45章 沈大夫窮得叮噹響
聽離王殿下的牆角,是要付出代價的,不管是誰,不論什麼份,這本就是離王府鐵打的規矩。
「當場被抓包。」沈郅補刀,慢悠悠的走到薄雲岫邊。一大一小,皆負手而立,低頭著坐在地上,麵發青的薄鈺。 「爹!」薄鈺膽戰心驚,眼睛裡滿是恐懼與慌,「我、我是路過,我不是故意要聽、聽你們說話的。爹,我不敢,我真的不敢,我沒這個膽子,爹你信我!」
「你是不小心走到了門口。」沈郅笑得涼涼的,「不小心聽到了什麼,不小心撲了進來,又不小心沒找好理由,說謊都不做準備,可見你這是有多敷衍你爹哦!」
說著,沈郅仰頭著薄雲岫,一臉的同與悲憫,「王爺這個爹爹,著實不好當呢!這是你們父子之間的事,跟我沒關係,我先走咯!」
正好能有理由跑路,不用回答薄雲岫的問題,沈郅何樂而不為?!
怪隻怪,薄鈺自己倒黴。
「哦對了!」沈郅已經走到了臺階上,又回頭沖著薄雲岫,語重心長的說,「我娘說孩子得自己教訓,若是借了別人的手,那是起不到作用的。言盡於此,好自為之!」
薄雲岫麵黑如墨,臨了臨了的,還得一個小屁孩來教他怎麼當爹?嗬……沈木兮養的兔崽子,這張皮子全隨了他母親,真是懟死人不償命。眸冷冽,低頭著腳下的薄鈺,薄雲岫周寒戾。
從院子裡跑出來,沈郅渾舒坦,著草螞蚱屁顛顛的往大牢裡去。
這會,春秀已經幫著沈木兮為阿落上了葯,現正蹲在大牢門口煎藥。
「郅兒,你幹什麼呢?這麼高興!」春秀搖著扇笑問。
沈郅晃了晃手中的草螞蚱,一溜煙的跑進了大牢,臨到之前,他了腳步聲,躡手躡腳的往裡頭走,想要嚇唬一下母親。誰知卻聽到了沈木兮哽咽的聲音,孃的鼻音很重,又是誰欺負娘?
Advertisement
沈木兮倒是沒哭,坐在床邊看著昏迷的阿落,如同百爪撓心般難,「你來時,說你是魏仙兒的婢,瞧著你的模樣與往昔無二,我還以為你的日子過得還算將就,卻沒想到竟是這般艱難。當年,難的時候是你陪我說話,痛苦的時候與我解悶,可我走的時候卻留下了你!」
阿落是伏在床上的,背上橫七豎八都是傷,有舊傷有新傷,非一日兩日所造,可見這些年阿落的日子並不好過。想想也是,阿落為的婢,在主子死後又怎麼可能到善待?尤其是在魏仙兒手底下當差,有些賬免不得會算在阿落頭上。
「阿落,對不起!」沈木兮低語。
沈郅詫異,定定的站在原地,娘原來和阿落是認識的?當年是什麼時候?是在他出生之前?可阿落是離王府的婢,娘是阿落的主子,那娘……難道是從離王府出來的?
思及此,沈郅捂住了,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難道娘和王爺認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細想起來,王爺非要帶娘去東都,娘死活不肯,百般懟上王爺,而那個壞人則一直欺負娘。
手中的螞蚱忽然落地,沈木兮猛地起,快速走出牢房。
「郅兒?」沈木兮愣住,「你、你什麼時候來的?」
「娘,你跟那個王爺是不是有什麼關係?」沈郅蹲下,撿起了草螞蚱。
驟見此,沈木兮瞳仁微,「你這個東西,是哪來的?」
沈郅著草螞蚱上前,遞給沈木兮,「視窗撿的,很漂亮,所以我很喜歡。娘,這跟你編得很像,但是比你教我的編得更好!」
「郅兒!」沈木兮言又止,手了兒子稚的小臉,「娘……」
「如果娘不好開口,郅兒不問就是。」沈郅抱著母親的腰,將臉埋在母親的懷裡,「娘在哪,郅兒就在哪,其他的事,郅兒一點都不關心。」
Advertisement
沈木兮抱了兒子,知道兒子想問什麼,可是有的顧慮,「郅兒,娘不希你卷進那些是是非非之中,娘隻希自己的兒子,平安喜樂,做個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你若是喜歡行醫,娘就教你治病救人,你若是喜歡讀書,娘就送你去學堂,無謂因為什麼人什麼事,而迫不得已的迎合!」
沈郅乖順的點點頭,仰頭著母親失去亮的眼睛,「郅兒不想讓娘擔心,也不會讓娘傷心,郅兒什麼都不要,隻要娘!」
「乖!」沈木兮紅了眼眶,「如果有一天,郅兒真的想知道真相,娘一定會告訴你的。」
「郅兒不想知道。」沈郅乖巧得讓人心疼,踮著腳尖,白的指尖輕輕去母親眼角的淚,「娘別難過,郅兒長大了,可以保護娘!郅兒,也會好好保護自己,不讓娘擔心!」
沈木兮牽著沈郅進門,「阿落不認得娘了,所以不知道娘是原來認識的那個人。郅兒就當不知道這些事,以後就喊作姑姑,像對待春秀姑姑那樣尊敬,郅兒能做到嗎?」
「能!」沈郅點頭,走到床邊,輕輕握住了阿落冰涼的手,低低的喊了聲,「阿落姑姑!」
沈木兮笑了笑,眼角有淚盈。
「娘,阿落姑姑什麼時候能醒?」沈郅問。
「傷得不輕,膏藥裡帶著安神的效用,所以一時半會不會醒。」沈木兮坐在床邊,將兒子抱在膝上坐著,「你能跟娘講一講,外頭的況嗎?」
沈郅點頭,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還有之前發生的事都一五一十的告訴母親,隻是當他提及了薄雲岫問他那個問題,孃的臉似乎不太好,沈郅有些擔心。
「你陸叔叔呢?」沈木兮問。
沈郅想了想,「這兩日,陸叔叔好似很忙,不是關在房間裡寫字,就是讓知書去送信,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不過陸叔叔說,他不會放棄的。」
沈木兮皺眉,「這話是何意?」
「不知!」沈郅搖頭,「娘被關在這裡之後,我便很看到陸叔叔笑了。」
「罷了!」沈木兮嘆息,抱了懷中的兒子,低頭親了親他的額頭,「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順其自然吧!」
沈郅不解,「娘,王爺為什麼派那麼多人圍著外頭,他不是真的想懲罰你,是想保護你對嗎?」
沈木兮沒吭聲,之前覺得薄雲岫是為了魏仙兒出氣,現在看來好像真的是在派人保護,且看看這大牢裡一個人都沒有,任一人在裡頭待著,許是薄雲岫察覺了什麼吧!
「對了,劉捕頭呢?」沈木兮問。
沈郅搖頭,「這兩日沒看到!」
沈木兮麵微,「沒看到?」按理說不太可能啊,難道說這中間又出了什麼變數?進來之前,劉捕頭知道要做什麼,這幾日應該會格外仔細。
「郅兒,你去把春秀姑姑進來,就說我有事找!」沈木兮放下沈郅。
沈郅應聲,撒就往外跑。
須臾,春秀搖著扇進門,「沈大夫,怎麼了?」
「春秀,幫我辦件事!」沈木兮伏在春秀的耳畔低語,「可都記住了?」
春秀有些張,「記住了!」
「郅兒!」沈木兮叮囑沈郅,「接下來這幾日,你跟著王爺,哪怕遠遠跟著也好,一定不要走出他的視線範圍,記住了嗎?」
沈郅愣愣的點頭,「娘,怎麼了?」
沈木兮瞇了瞇眸子,呼吸微沉,「怕是要出事!」
春秀搖了搖扇,心躁得慌。
傍晚時分,阿落醒了,春秀給阿落餵了葯,這才帶著沈郅離開了大牢。
阿落定定的看著沈木兮許久,始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沈木兮也不著急,隻是在旁靜靜的陪著,阿落不說話,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更怕自己一開口便會忍不住心中。
從牢房出來,春秀把沈郅送到了薄雲岫的院子外頭,瞧著杵在門口跟門神似的侍衛,春秀討好般乾笑兩聲,卻惹得侍衛如同見鬼般盯著。
春秀滿麵尷尬,「能勞煩諸位好漢一件事嗎?我這廂有點事,又放不下我家小朋友,能擱在這兒,煩勞諸位點心,幫著看會唄?」
「春秀姑姑,你去忙吧!」沈郅乖乖的坐在門前臺階上,「娘叮囑過的事兒,我都記著呢!放心吧,這次我絕對不會自己跑掉的。娘還在牢裡,我不想讓為我擔心!」
「真乖!」春秀深吸一口氣,「那我先走了,你注意安全。」
「嗯!」沈郅點點頭,將草螞蚱放在自己邊,如同好朋友一般與自己作伴。
侍衛們麵麵相覷,一時半會的鬧不明白他們在幹什麼,猶豫著要不要稟報王爺?可一想起王爺之前發的火,連小公子都加以懲罰,若是再去王爺的黴頭,不定要怎樣的責難。
不去不去,誰都不敢去!
許是一個人坐在臺階上無聊,過了一會,沈郅蔫蔫的有些發困,靠在了門口直打瞌睡。突然間子一晃,一腦門往地上栽去,好在有人眼疾手快,急忙有雙手捧住了孩子的臉。
沈郅睡意朦朧的嗯嗯了兩聲,了自個的眼睛,一臉的迷濛。
黍離吐出一口氣,「嚇死我了!沈公子,你要睡也該回房去睡,坐這兒幹什麼?」
「娘說讓我跟著裡麵的人,確保自己的安全!」沈郅指了指院子。
黍離皺眉,「你娘讓你跟著王爺?」
沈郅點了點自個的小腦袋,犯困的同時還不忘把草螞蚱抓回來,攥在手裡,「娘說,不能離開他的視線範圍,隻有這樣才能確保我安全無虞。娘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我不會礙著你們什麼事,我就在這兒坐著,我很乖的,不會吵到你們的!」
「你等會,我去稟報王爺!」黍離起就走。
沈郅也沒打算薄雲岫會收留他,反正娘說隻要在附近就,等著春秀姑姑辦完事就會來接他的。撓了撓脖子,沈郅靠在門口,懶洋洋的合上了眼睛。
夜靜謐,春秀小心翼翼的推開李捕頭的臥房,這些日子發生了太多事,所以李捕頭並沒有回家,橫豎他是孤家寡人一個,乾脆就住在府衙裡。
床褥沒有過,枕頭底下放著一個平安符。
按照沈木兮的吩咐,春秀又開啟了櫃子,搜尋一番之後,便蹲下子,檢視著床底下的鞋子。指尖從鞋底掠過,湊到鼻尖輕嗅。臨了,春秀站起來拍去上的塵土,在屋子裡慢悠悠的饒了一圈,這才疾步離開。
春秀回了大牢,氣息有些微,「沈大夫!」
「如何?」沈木兮忙問。
春秀搖頭,「枕頭底下有一個平安符,櫃子裡沒有服,床底下擺著一雙鞋子,但是鞋子底部很乾凈。不過我在屋子裡倒是聞到了你說的那香味,就是淡淡的,說不清楚是什麼花的味兒。」
沈木兮輕哼,「果然如此!」
「果然什麼?」阿落開口。
二人齊刷刷盯著阿落。
「是你們幫我上藥?」阿落坐在床角,雙膝曲著,子在冰涼的牆壁上,說話的時候眼皮子也是半垂著,整個人看上去懨懨的,很是沒打采。
春秀眉心微蹙,略帶不解的著沈木兮。
「你覺得好點嗎?」沈木兮問。
阿落仍是低著頭,但還是說了句,「謝謝!」 見狀,沈木兮和春秀對視一眼,頗有些無奈。
「春秀!」沈木兮伏在春秀的耳畔低語。
「非要這樣?」春秀皺著眉,「怕是不好請,他會信我嗎?」
「會!」沈木兮深吸一口氣,「他一心要回東都,這裡的事自然是越快完事越好。你隻要說明意思,他一定會答應的。」
「好!」春秀轉,想了想又不太放心的回頭著沈木兮,「那你呢?」
「外頭都是侍衛,我能有什麼事?你趕去,記得幫我看好郅兒!」沈木兮說這話的時候,眼睛裡的神有些複雜,袖中雙手微微蜷握,但麵上仍是雲淡風輕之。
待春秀離開,沈木兮臉上的笑意漸漸散去。
「你是別有目的。」阿落說。
沈木兮回頭看,「你也該走了!」
阿落抬頭看,眉心皺得的,「不知道為什麼,我看著你,總覺得好像是認識的。」
「許是一見如故!」沈木兮沖微微一笑,心裡卻煙雨迷濛。
阿落,阿落,我是——夏問曦啊!
可惜,阿落聽不到心裡的聲音,也不敢讓阿落知道,畢竟在所有人的眼裡,世上早已沒有了夏問曦此人,現在是沈木兮。
阿落走了,大牢裡又隻剩下沈木兮一人。略的估計丹爐裡的花,應該已經長,是製蛇毒解藥的唯一藥引,那些人應該很想得到它!之前陸歸舟不是說了嗎?花!
是的,這就是那些人想要得到的花,開在死去的蠱蟲載上,一朵朵晶瑩剔的,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死亡之花!能讓人生,也能讓人死。
安靜的夜,讓人莫名的心悸。
沈木兮靠在牆壁上,疲倦的合上眼睛,也不知過了多久,外頭忽然想起了一陣細碎的聲響,伴隨著令人厭惡的「沙沙」聲!
房。
薄雲岫冷眼著春秀,春秀梗著脖子,「你到底答不答應?」
「放肆!」黍離低斥,「爾等豈可對王爺無禮!」
「是說的?」薄雲岫幽然開口。
春秀連連點頭,「是沈大夫代的,說劉捕頭提過,那張平安符是他母親留下的,所以出門時都會隨帶著,但夜裡睡覺必在枕頭底下,素來不離。劉捕頭不在房中,但是平安符卻還在,所以劉捕頭很可能是夜裡睡覺的時候著了道!」
這麼一聽,的確有些道理,黍離問,「那櫃子是怎麼回事?」
「劉捕頭孤家寡人一個,我們與他也算相,他家裡沒什麼人,眼下自個住在府衙,按理說應該帶上一兩套裳替換,但是現在櫃裡空空如也,說明有人拿走了他的裳,至於為何拿走自然不需要多問,有真假陸歸舟的先例!」春秀所說,皆是沈木兮所授,言語間有理有據。
黍離點點頭,皺眉著薄雲岫,「王爺,看樣子真的是有人冒充了劉捕頭。」
「此前劉捕頭經常走,這兩日倒是不怎麼見著蹤跡,不像是劉捕頭古道熱腸的格。」春秀繼續說,「劉捕頭床前的鞋子是乾淨的,但是屋子裡卻有一葯香,那是沈大夫刻意在後院佈下的,倒也不是小氣,隻是擔心萬一有人手腳不幹凈,拿了葯廬裡的好東西出去販賣。」
黍離想了想,「你是說擱在後院的,沈大夫葯廬裡搬出來的東西,被人過了?」
「是!」春秀點頭,「知道那是離王府搬出來的,試問誰敢輕易去?」
薄雲岫麵陡沉,那便隻有長生門的人!隻不過,為什麼要去翻找葯廬裡的東西?是在找那個青銅鑰匙?又或者別的什麼目的?橫豎,是在找東西!
驀地,薄雲岫麵驟變,風似的衝出了房間,「去大牢!」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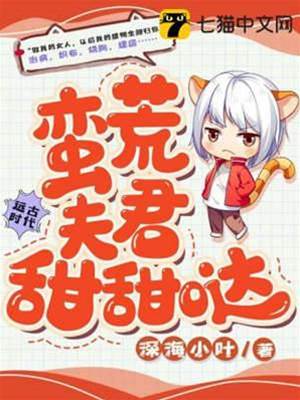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321 -
完結154 章

二小姐進京了
沐羨之穿成了沈相爺家多病,從小養在山上道觀里的二小姐。彼時沈相夫妻剛去世,面對龐大的產業,親戚們虎視眈眈。性格軟弱的長姐被欺負得臥病在床,半死不活。要面子好強的三妹被退了婚…
52.8萬字8 23836 -
完結571 章

滿門炮灰讀我心后,全家造反了
喬嬌嬌上輩子功德太滿,老閻王許她帶著記憶投胎,還附加一個功德商城金手指。喬嬌嬌喜滋滋準備迎接新的人生,結果發現她不是投胎而是穿書了!穿成了古早言情里三歲早夭,戲份少到只有一句話的路人甲。而她全家滿門忠臣皆是炮灰,全部不得好死!喬家全家:“.......”喬家全家:“什麼!這不能忍,誰也不能動他們的嬌嬌!圣上任由次子把持朝綱,殘害忠良,那他們就輔佐仁德太子,反了!”最后,喬嬌嬌看著爹娘恩愛,看著大哥 ...
105.3萬字8.18 17807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5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