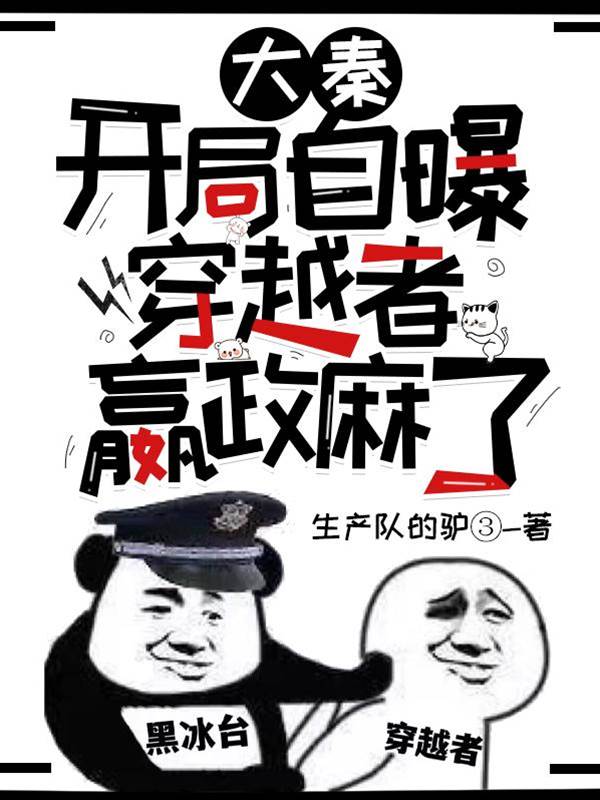《名醫貴女》 263,新的聖女
到底是誰膽大包天衝奉一教營地揍了聖,還把聖活活揍了個豬頭?不是雲飛峋又是誰!?
雖然並未得到證實,但在蘇漣漪心中,已經定了雲飛峋的罪。
試問,若不是雲飛峋手下的影魂衛,誰能在戒備森嚴的營地來去自如?而爲何單單對聖下手而兩位嬤嬤安然無事?爲何不傷聖卻只打臉?
懶得理會安蓮的蘇漣漪,無奈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手著自己太——飛峋啊飛峋,你最近吃錯了什麼藥?從前那穩重又懂事,懷如海的飛峋到底哪去了,請不要把這狡猾易怒的男人扔來霍霍人好嗎?
“小漣,你去哪裡?”停止了哇哇大哭的安蓮一把抓住正準備離開的蘇漣漪。
漣漪低頭看安蓮的樣,非但沒有平日裡的淡淡反,還覺得可笑又心疼,“聖大人別哭了,這些都是皮外傷不會毀容,一會我代孫嬤嬤們爲你消腫,我有急事必須出去。”
安蓮的哭聲真的小了一些,“真的……不會……毀容?”
“恩,我發誓不會毀容。”漣漪向其保證。
“那……那你辦完事馬上回來好嗎?”安蓮就是不想讓小漣離開。
“好,辦完事就回來。”漣漪無奈道。
終於擺了安蓮,又對兩位嬤嬤代相關事後,漣漪二話不說,怒氣衝衝地奔向了雲飛峋的獨立營帳。
自從被提升爲侍衛長,雲飛峋的待遇順勢提升,其中包括有了獨立的營帳,方便了他許多,行也自如了許多。從前,雲飛峋想見蘇漣漪或到營外與手下們見,都要十分小心地溜出去,提前還要編好理由。但現在卻不用,夜後直接行便可。
Advertisement
若是以往,營地中滿是巡邏的人或把守的人,但今日營地卻是靜悄悄的鮮有人,那些好事之人都跑到聖那裡看熱鬧,而不好事之人還在睡覺。於是,蘇漣漪就這麼大搖大擺又無人察覺地進了雲飛峋的帳子。
帳,桌上點著油燈,不是很亮,但守夜已足夠。
雲飛峋安安穩穩平躺在牀上,被子蓋到前,閉雙眼、呼吸綿長,讓人不知其到底在安睡還是裝睡,畢竟屋外聲音不小。
蘇漣漪見狀,更是落定了雲飛峋的罪狀。
“雲飛峋!”漣漪咬牙切齒地喊著他的名字,能不氣嗎?潛伏營求的就是一個潛伏,不得明到讓所有人當自己是空氣,但云飛峋可好,大半夜把人家聖給揍了。
本來面容暗想的飛峋勾起了脣,帶著許多狡猾。“漣漪聲音這麼大,是不是怕別人不知我們的份?”
蘇漣漪臉紅了下,趕忙向窗外張。好在,窗外無人。
“飛峋,你……你……太讓我失了!”漣漪低了聲音。
雲飛峋睜開了眼,那雙深邃的眼,帶著許多戲謔,平日裡銳利的目此時化作溫,貪婪地黏在自己人上,不忍離開。“爲夫有什麼讓娘子失的?說來聽聽。”
蘇漣漪氣得了拳頭,“飛峋,爲何這一次東塢城一見,我發現你變了?”
飛峋坐起來,上穿著淡薄裡,純白又合的裡,將他完材勾勒得更爲修長,寬肩,細腰,窄,即便是隨意一個坐姿也能鏡,何況還有那一雙吸引人的長。
“變?”飛峋修長的手指了自己下,下上有淡淡的胡茬,非但不覺野蠻,反倒讓他有種平易近人的可。他真的好像很認真的思考了下,而後皺了皺眉,“我的人是沒變的,只不過從前一直憋著。但漣漪你也知道,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憋啊憋啊,有一日就發現自己憋不住了。”
Advertisement
漣漪拳頭再次,“雲飛峋,你說實話吧,外面發生什麼事,你可知道?”
飛峋挑眉,一臉的無辜加欠揍表,“不知,我正睡著,什麼都不知道。”
蘇漣漪深吸一口氣,“也就是說,是你派你手下人做的,對嗎?”
“影魂衛啊,”飛峋一拍手,好像想到了什麼似得,“很久沒見了,不知他們最近過的好嗎。”
蘇漣漪哭笑不得,見他貧,本來怒氣騰騰的火氣,一下子也消了大半。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衝到雲飛峋邊,一把揪起他的耳朵,“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爲什麼派影魂衛打人?”
“哎呦呦……”飛峋呲牙咧,其實耳朵上這點疼,他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他的忍耐力比一般人不知強多倍,但此時他是裝作被得很疼,只爲博得人的歡心。“好疼好疼……”
漣漪見他吃痛,趕忙放輕了手勁兒。“回答我,爲什麼讓影魂衛打人?”
飛峋見漣漪都猜到了,也就不瞞著了,“還能因爲什麼,得罪我了。”
漣漪哭笑不得,爲什麼覺得雲飛峋此時和孩一樣無理取鬧?鬆開了他的耳朵,坐在他旁的牀上,“人活在世,怎麼可能順心?只要沒牴原則,能忍便忍。從前,這一點你做得比我好,你的忍耐力比我要強上幾倍,爲什麼現在這麼關鍵的節骨眼,你卻如此衝?”
飛峋扭過頭,“漣漪你說的沒錯,人活在世不會順心,但人生短短百年,爲何又要無休止的忍、無理由的忍?若無力與之爲敵,即便委曲求全也不爲過,但既然有能力,又有什麼理由讓那人無憂無慮的活著?”
這是蘇漣漪第二次聽到雲飛峋如同洗腦一般的長篇大論,第一次是在那次針對聖的聚會上。如今,也忍不住反思,關於男人是否表裡如一的問題,爲何當初的親,有種上當騙的覺?
“飛峋你說得沒錯,但報仇也要看好時機不是?若現在我們二人並非潛伏份,那你大可以派影魂衛出手,甚至殺了也行,我蘇漣漪也不是慈善的聖母。問題是,你現在了,整個營地戒嚴,有更多雙眼睛盯著我們,我們還如何行自如?”漣漪反問。
雲飛峋也知,出了手就沒有挽回的餘地,往後他的行不會太過自由了。“但……今日見到……算了,我……沒親自手,已是強忍的結果。”斷斷續續的說著,想到腦海那一幕幕,他連將其挫骨揚灰之心都有。
漣漪到偌大的木牀微微抖,可見其忍耐的艱難。
蘇漣漪自責,奉一教之事與飛峋全無關係,但他來此完全是因爲,而還對飛峋如此苛刻,想來,是自己的不對。
手攔住他結實的細腰,將臉埋在他的懷。“飛峋,你平日極是潔自好,自從認識你到現在,從未聽說你與某家閨秀有毫瓜葛,這一點,別說鸞國,即便是整個天下,也不會有第二個男子做得有你好。我能嫁給你,是我的福氣,真的。”
飛峋哼了一下,帶著傲的分——知道就好。
漣漪繼續道,“聖對你的心意,我也知道,起初我也擔心,聖容貌不錯,在男之事上也是個老手,怕你不住的。但隨後我發現,我真是大錯特錯,雲飛峋永遠那個雲飛峋,永遠是那個值得我委以終的雲飛峋。”
飛峋所有火氣,徹底平息,一頭雄獅已功轉化爲順的小貓,著爪子,討主人的好。“漣漪,我會終其一生,對你好。”雙臂環繞了。
安蓮鬼哭狼嚎聲越來越小,營地逐漸恢復了平靜,到有走聲,想來是看熱鬧的侍衛們逐漸散去,回到各自崗位。
漣漪趕忙從飛峋懷中掙出來,重新正道,“言歸正傳,無論你如何強詞奪理,但這件事分明就是你的不對,你承認嗎?”
飛峋低頭,不吭聲。
漣漪又道,“就算是平日裡纏著你,但也是因爲慕你,即便你再厭惡,也不能派人揍。還有,捱了揍,作爲侍衛長的你,難道就能離干係?”
本來準備默默被責罵的雲飛峋突然擡起頭,“等等,漣漪你說什麼?什麼纏著我?”
蘇漣漪也是一愣,“聖安蓮啊,因爲平日纏著你,還對你下了催藥,所以你派影魂衛趁夜打了。”
飛峋一下子從牀上站了起來,“漣漪,難道你就如此看我?我雲飛峋也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怎麼會對一名子手?”
蘇漣漪也站了起來,到雲飛峋面前,滿是驚訝,“你不是說……你派影魂衛手打人了嗎?”
“對,我確實讓他們出手了,但打的是玉容,”雲飛峋答,一提到玉容,便想起他將披風披在漣漪上的景,若非條件不允許,他非親手殺了那人不可。
“啊!?”蘇漣漪終於沒忍住,驚訝出聲,“你派人打了玉護衛!?”
飛峋見漣漪作勢要袒護玉容,開始吃醋,“對啊,不可嗎?”
漣漪哭笑不得,“飛峋,聖的鬼哭狼嚎,難道你沒聽見?”
飛峋一挑眉,“聽見啊,聖與玉容關係曖昧,那人定是見到玉容被打才哭的,不是嗎?”
漣漪搖頭,“不是,不是,聖哭,是自己被揍了!”
“……”飛峋一愣,“自己被揍?”趕忙解釋,“我可沒讓影魂衛對聖出手,我一個男人怎麼和一人過不去?而且我敢保證影魂衛的執行能力,沒有我的命令,他們不會擅作主張做其他事。”
“也就是說,聖不是你下手?”漣漪頭上霧水越來越多。
飛峋狠狠點頭,“我雲飛峋對天發誓,若派人打聖,便不得好死!”
蘇漣漪跌坐在牀沿,“那會是誰打了聖?聖平日裡真是鮮出門,哪有機會得罪人?”首先,蘇漣漪想到的是兩個嬤嬤,畢竟兩人都恨著聖,但剛剛的形親眼所見,兩個嬤嬤也是被綁得結實,已經排除了可能。
雲飛峋也思考這個問題。
“哦,對了,”蘇漣漪猛的想起,“飛峋你在房千萬別,以免被人懷疑,我現在去看看玉護衛的況……啊!”話還沒說話,便是雲飛峋一個翻,狠狠在牀上。
“不!許!去!”雲飛峋雙臂撐著,將漣漪在下,低頭認真盯著蘇漣漪的爽呀,一字一頓道。
漣漪自然知曉雲飛峋在吃醋,手了他的下,那胡茬很好玩,“飛峋難道你不信任我嗎?我已嫁給了你,便心都是你的人,一生一世,絕不會背叛你,哪怕是再大的。”
雲飛峋聽漣漪的表白,開心雀躍,卻依舊不想放人。
“我知道,最近我和玉容走得近了一些,我也不想這樣,”漣漪也是苦惱,“再給我一段時間好嗎,我會加進度,一旦拿到我想要的信息,我們便立刻離開營地。”
雲飛峋不語,但倔強的眼神已經逐漸和。
漣漪笑著,手環住他的脖子,在他胡茬的下上輕輕一吻,看著他賭氣吃醋的樣子實在可,“事到如今,若輕易放棄那便真是前功盡棄,你也不希我們最後空手而歸回到京城吧?你也不希看東塢城百姓繼續被這詭異的奉一教愚弄吧?難道你不想知道奉一教背後的謀到底是什麼?”
雲飛峋掙扎了下,最終嘆了口氣,將漣漪放了開。“我真沒用,看著你被其他男人糾纏,卻束手無策。”
漣漪撲哧笑了,“飛峋你錯了,一個人到底是否有用,是看能否管住自己而非其他人。若按你的理論,那些朝三暮四的男子都沒錯,錯在他妻子,是因其妻沒能力所以男子出外拈花惹草,你說對嗎?”
雲飛峋失笑,“罷了,我說不過你,你贏了,行了吧?”
漣漪挑眉哼了下,“現在說你口才不好,我纔不信。只不過我說得更有道理罷了。”
飛峋卻笑不出來,心中酸溜溜的,“那你要去玉容那裡?”心中卻後悔,爲何不直接代影魂衛把玉容活活打死。
能將雲飛峋心猜的七七八八的漣漪撲哧笑了,“好了,別吃醋了,我只是去看一眼,聖還等著我回去呢。”
最終,雲飛峋無奈同意,爲了減嫌疑,他未出營帳半步,而是矇頭睡了大覺。但真正能否睡著,便只有他自己知曉了。
蘇漣漪匆匆趕往玉容的營帳。
帳一片漆黑,爲玉容把守的侍衛都被打暈,即便營發生如此大聲響,侍衛們都沒醒,可見影魂衛們下手之重。
到了門口,漣漪調整了下緒,而後裝作慌張一般,一下子衝了進去,“玉護衛,玉護衛您在哪裡?玉護衛您沒事吧?”聲音滿是擔憂。
室一片黑暗。
漣漪出火石,點上燈,線逐漸亮了起來。藉著亮,漣漪看到地上被五花大綁的玉容,和李嬤嬤孫嬤嬤兩人的待遇很是相像,頭上蒙著袋子。
“玉護衛!”漣漪一邊驚,一邊將玉容頭上的袋子取下。
袋子,玉容面容毫無損傷,只是面蒼白如紙,一雙眉皺,臉上有薄薄一層冷汗,想來是在忍無比疼痛。
漣漪不敢怠慢,趕忙將其上的繩子解開。“玉護衛,您……醒著嗎?”漣漪小聲、遲疑的問,因能覺到玉容渾微。
想起了上一次幫玉容鬆綁時的景。明明一日一夜未吃未喝未如廁,甚至連都未一下,但玉容依舊在牀上安靜的躺著,其驚人的意志力,是蘇漣漪從未見過的。
這一次,玉容也是在忍耐疼痛。
漣漪見玉容還未言語,猶豫了下,“抱歉,玉護衛,得罪了。”說完,便手解玉容的服。
玉容本在睡眠中,穿得單薄,蘇漣漪幾下便將他剝得乾淨,只餘。
只見面蒼白的玉容雙頰突然爬上紅,忍不住睜開眼,忍著疼痛,從牙中出幾個字,“你……做什麼?”
玉容材雖不若雲飛峋那般健壯完,但結實修長的也是極爲養眼,可惜,在蘇漣漪眼中,玉容只是個病人,沒有別。
“別,我先簡單爲你檢查下。”漣漪一邊輕輕玉容腫脹的手臂,一邊道。手臂腫脹,應是淤,千萬別碎骨折。
將手移到其膛,輕輕按下了下,“這裡,疼嗎?”爲其檢查肋骨是否斷裂。
“嘶——!”即便是忍耐力強的玉容,也忍不住疼出了聲音,全繃幾乎到痙攣。
猜你喜歡
-
完結701 章
回到明朝做昏君
穿越大明朝,成爲了木匠皇帝朱由校,那個,我躲在後面,背黑鍋我來,送死你們去。
203.6萬字8 19867 -
完結391 章

穿越后我捧紅了十八個大佬
全能經紀人被迫穿越,手底下居然只有一個十八線藝人。 趙星表示,大不了從零開始,再創神話。 十八線沒名氣?沒關係,大資源一個接一個,總能讓你逆襲一線。 古代穿越而來,沒法融入社會?莫著急,成為她的藝人啊!輕鬆讓你融入現代社會,受萬人追捧。 曾經巔峰已過氣?小意思,跟她簽約啊,七十二種複出方案,每一種都可以讓你重臨巔峰。 被人封殺黑料多?小問題,只要你不是個人渣,只要跟她簽約,都讓你突破困境。 …… 作為造星神話,所有人都說她善於打造寶藏。 但趙星卻說,她捧紅的偶像,就是寶藏本身。 十八線是真正的富三代,穿越來的白衣公子竟是古國全能國師,過氣巔峰是財團董事,就連被封殺的小可憐都有高名氣小馬甲。 帶著這一群寶藏,趙星覺得絲毫不能彰顯自己的能力。 所以,她將目光放在了某個大佬身上,想拉他進圈,卻不想被大佬給拉回了家…… 事業無限發展,感情線1V1(敲重點!1V1)
72.1萬字8 7755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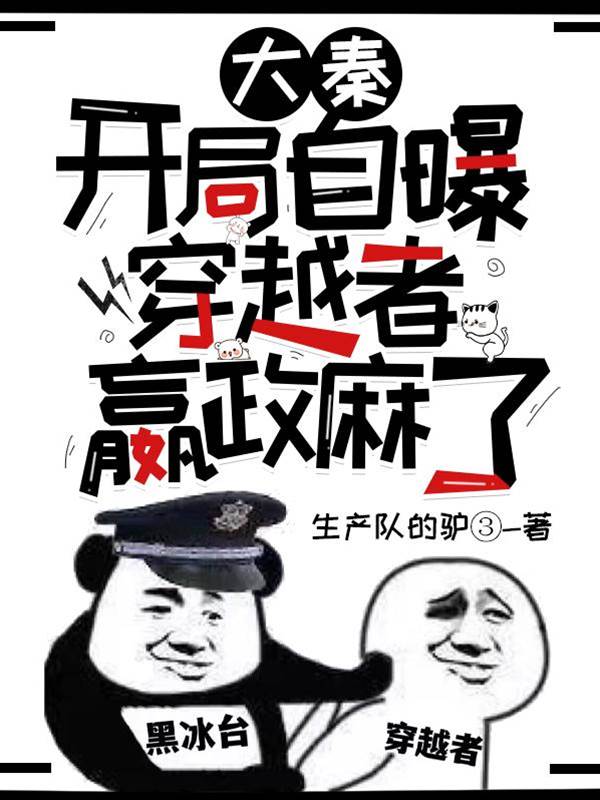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